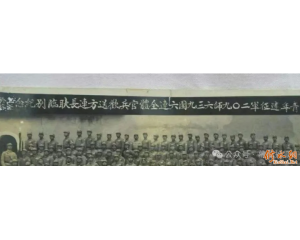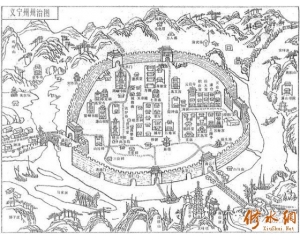|
常记起过去看戏的岁月,特别是看家乡的宁河戏。 那时乡下人看戏很难得,要县里的宁河戏剧团来了才有得看;所以,平常丰收喜庆、过年过节的要看戏,就只能请当地的农民业余剧团了。现在,县里的宁河戏剧团早就解散了,农民业余剧团也很难像当年一样各地都能筹建,所以看戏就更难了,只能在电视里看看京剧、越剧、黄梅戏等过过戏瘾,家乡的宁河戏除了一些中老年人一块聊聊,一同怀念,就只听说全丰镇有个农民剧团偶尔演演,或是县里的票友抢救性的演出片段了。不过,最近看到一个消息,说是溪口镇被九江市定为宁河戏非遗传承基地,并且开始招收学员培训宁河戏演员和乐队,这倒是让我们燃起了希望——宁河戏能传承下去,又会有宁河戏看了。 宁河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地方戏剧种,只是在九江市修水县才有。当年除了县里有一个正规的宁河戏剧团,各公社几乎都有农民业余剧团,大多都演宁河戏。 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我已有五六岁,能记事了),我的老家上奉公社有一个农民业余剧团,他们白天生产,垦山种茶;晚上排戏,巡回演出。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宁河戏《定军山》《拾玉镯》《柜中缘》《平贵回窑》等,还有黄梅戏《天仙配》《打猪草》《夫妻观灯》,新编现代小歌剧《一袋米》等。这些大戏小戏吸引了村里的男女老少,一听说哪里搭起了戏台,便早早吃过晚饭,邀三串四匆匆赶了去,围在台边看戏班子的人怎样灌煤油打气把“汽灯”点亮,怎样挂幕布、架锣鼓、给胡琴定弦;最爱看的是演员化妆,油彩笔一勾一画,一张神奇的脸谱就出现了。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等到台前挂起了两盏雪亮的、发着“丝丝”响声的汽灯,看戏的人群也打着火把或电筒沿着蜿蜒的小路游龙般陆续来到了台下。一个戏班子的人撩开幕布看了一眼乌压压的人群再缩回去,台侧就响起一阵急骤的牵人心弦的“闹台”——开场锣鼓。 这时,台下的人便陆续熄掉火把。有近处带了长凳的就坐在凳上,抽着旱烟耐心地等;或车转头寻找亲戚朋友,大呼小叫:来这里坐,给你留着凳呢!远处带不了凳的则有的找个打谷的方桶翻转来坐下,或找块大石头或摞几块断砖,解开腰里揩汗的大手巾垫上,也坐下;有的就伸长颈项四处张望,寻找熟人凑热闹;还有的小伙子甚至爬到树上,坐在树杈里,居高临下的看着上不来树的大姑娘小小子们好不得意。 不一会,大家都找到了合适的所在,于是都眼巴巴地望着台上的幕布,盼着它早点拉开。 幕布一拉开,在锣鼓和胡琴唢呐的音乐声中,各种角色粉墨登场,咿咿呀呀唱起来,舞台下就安静了,大家都伸长脖子认真看戏,生怕漏掉了哪一处精彩。 成立公社的那年,为搞庆祝活动搭台唱戏。那年我刚进小学不久,也表演了《拔萝卜》里的老公公。小节目演完后是业余剧团唱大戏,剧目是宁河戏《定军山》。由于剧团人手不够,摇旗喝班的角色(戏中的龙套)都是临时拉人凑数。我还未来得及下台,就被拉去喝班。白胡子的黄忠和花脸夏侯渊在台中间打得难解难分,我在台边上吓得脸色煞白,只是被另一个喝班的大人推着转。事后我的同学及邻居都夸我,说我小小年纪就唱大戏了,了不起!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在县城的修水中学,这给了我看宁河戏的绝好机会,一年总能看几次。读三年初中,我先后看了县宁河剧团演出的《白蛇传》《三气周瑜》《穆桂英挂帅》《闹天宫》《闹龙宫》等古装戏,也看了《江姐》《南海长城》《芦荡火种》《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等现代戏,还有他们自己创作演出的《白云深处》《春风化雨》《幕阜风雷》《海舟过关》等新编戏。 那时看戏,有时是学校包场,有时是周末自己买票去看。大人一张票三角钱,学生票只要一角五,我总是尽量在其他地方节省,舍得花钱去看戏。 不知为什么,比起看电影来,我更愿意看戏,虽然电影票只要一角钱,比看戏便宜。也许是当时的电影大多是黑白的,偶有彩色的也色彩质量不好,总给人一个看虚幻的影子的感觉,而看戏却有强烈的现场感,可以同剧中人一起同哀愁,共快乐。我常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感动,常被宁河戏的唱腔和伴奏感染,常被宁河戏的程式化动作吸引,沉浸在戏中,往往出了剧场耳朵里还满是唱腔和锣鼓声,眼前也还浮现着演员或飘逸或刚劲的动作和身影。 文化革命破四旧,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统统赶下了舞台,焚毁了传统戏装,县宁河剧团只能演有限的几个现代戏剧目,农村的业余剧团自然也解散了;可是,乡亲们看戏的热情仍未减退。上边刚刚说普及样板戏,一些有原业余剧团“主力”演员的大队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起了样板戏。剧本是样板戏,唱腔却学不会京剧,只好援用业余剧团时唱的宁河戏、黄梅戏、采茶戏的混合腔,倒也唱得有声有色。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由于我有过一次“唱大戏”的经历,于是把我拉进了宣传队;又由于我在县城读过书,看过不少戏,就要我协助一位原业余剧团的老演员导演《红灯记》,并扮演剧中的鸠山。另外,宣传队还让我和另一个原业余剧团的人合作自编了一出歌颂焦裕禄的大戏《红色种子》。这出戏完全是按宁河戏的路子来写的,所以从唱腔到动作,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宁河戏。虽然很业余,服装设备都很简陋,但由于实在是没有戏看,仍然很受欢迎。 粉碎“四人帮”后,县宁河剧团恢复了下乡演出,照例各大队都要演出一两场。当时轰动的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乡亲们场场追着看,从这个大队追到那个大队。 有天晚上,在山背大队演出,我们去的时候有月亮,回的时候却下起了小雨,天像泼了墨似的黑。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在田间小路上往回摸。走到一条小河边,要过一座用三根树拼成一节的多节小桥。小雨淋湿了桥面,很滑,加上天黑,大家只好趴下,两手摸着桥板,一步一步往前爬。虽然到家后是一身水一身泥,但都觉得无比舒畅,因为又过了一回戏瘾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宁河戏有过一段振兴的时期,那时不仅是恢复了古装戏的演出,现代戏也演得很红火,可演的剧目增加到了三四十个。县里还创建了宁河戏中等专业学校,招收了一批学员,每日里练功吊嗓学戏,也有一些学员就此脱颖而出,成了宁河剧团的新秀。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后来,电视兴起了,县宁河剧团渐渐处于竞争的劣势了,演一场戏的支出远远超过卖票的收入,越演越亏本了。县里也以文化产业改革为由,断了给宁河剧团的财政补贴,于是剧团只能落个解散的下场,乡亲们基本上看不到戏了。 虽然电视里也有时播放一些戏剧片段或戏曲连续剧,但是毕竟不是舞台演出,氛围不一样。完整的大戏要戏曲频道才会有,而戏曲频道乡下又因为没有闭路有线电视或是没有网络又收不到,农民要看到大戏就更难了。家乡的宁河戏也就逐渐濒临绝迹了。 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剧团拍过一个《秦琼表功》的戏曲电影,老艺人晏纯珠饰演秦琼,这很可能是当年宁河戏留下的唯一音像资料了。 近些年,有热心的群众自发搞起了票友社,全丰镇溪口镇还有农民自发办起了业余剧团,聘请一些宁河戏老艺人传授,继续传承宁河戏。时不时的,又能听到一些唱戏的声音了。 虽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爱上了唱歌跳舞,自娱自乐,不太看戏了,这主要是因为无戏可看;不过,依然有人喜欢看戏听戏,特别是中老年和广大农民,他们渴望能经常看到大戏,更渴望能经常看到家乡的宁河戏! 晏建东,男,1952年出生,1966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江西文学特约作家》。1978年经考试走上讲台,后自学获得大专毕业文凭。多次参加全国和省教改研讨会,后调入修水一中任教,于2012年退休后定居南京。在全国各种教学期刊发表教学论文多篇,在《江西日报》《九江日报》《中国教师报》《摇篮文学报》《鹃花》《浔阳江》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近年在《中国京剧》发表剧评两篇。共计逾百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