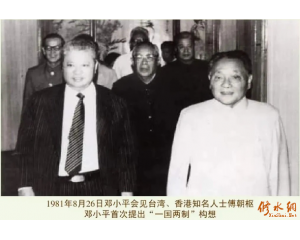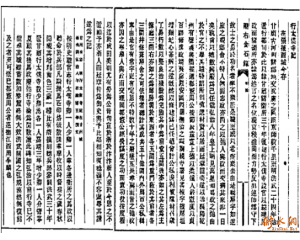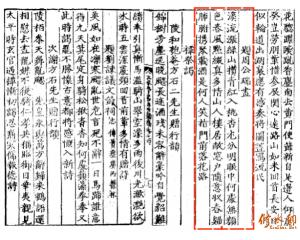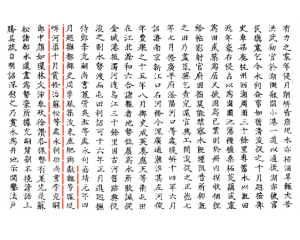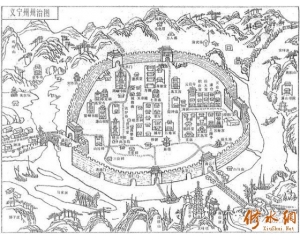|
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家乡安放不下肉身,他乡容纳不了灵魂。”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家乡找不到养家糊口的门路,找到了养家糊口门路的地方却安不了家,从此便有了漂泊,有了远方,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有了太多的不舍与无奈,若能一世安稳,谁愿颠沛流离在他乡啊! 出生至今六十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修水,因而对这一无奈而又痛苦的说法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想到身边很多朋友离乡背井去外打拼,很多同学漂泊异乡去陪伴孙儿,不免对这个问题做一番思考,因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记得1978年之前,国家限制人口的流动。单位人员出差,老百姓出外办事,必须出具单位或公社的介绍信,如果出省,还需兑换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因而大家都被迫固守在家乡的一亩三分地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外打工浪涛汹涌,大家纷纷涌向江浙沪和广东等沿海开放经济发达之地。而家乡还有小孩要上学,老人要照顾,一家夫妻二人只好一人出外,一人留守家乡,从而夫妻被迫天各一方分居两地。漫长的一年中,只能春节期间见上一面,和家人团聚几天。有的甚至几年回来一次,夫妻之间的相思、对家人的牵挂,只能交给书信和电话。 这一状况延续至今,依然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肉身和灵魂还是只能无奈地痛苦分离,很多离开家乡的人们依然还在矛盾和痛苦之中苦苦地挣扎。夜阑人静之时,有多少人相思难寐而泪湿枕巾,有多少人辗转反侧而梦回家乡。 周湖岭 由此,想到自己以前一些和此相关的事情,并由此产生的一些感受,似乎也和肉身及灵魂相关。 那是2014年,当时本人是县政协委员。政协组织一次专题调研考察,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先在县内调研,后去这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河南洛阳和兰考等地考察学习。来去的时间大概个把星期,先到洛阳、嵩山、郑州,后到开封、兰考。开头几天无所谓,后来感觉人不得劲,又没有什么病,就是有点不舒服,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从嵩山出来后,一直都在平原上跑,华北大平原天高地阔,坦荡如砥,不管跑多久,除了平原还是平原,好像总是跑不出平原的手掌心。兰考之后,就是回程之路,好像是车子快到安徽的六安,远远地看到大别山的影子,感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的感觉在渐渐消退,当看到远方苍茫的大山时,那种感觉才彻底消失。这时,我才突然顿悟,原来是这么多天没有看到山的缘故,真是令人发笑。 自己真是一个山牯老!从出生到现在的六十多年里,几乎每天都是出门见绿,抬眼是山,生在山中,长在山里,山青树绿碧水清波已经深深地融进了生命,成为了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灵魂必须和修水的山水在一起,才会安置妥帖。 湖岭 早几年,经常往九江跑,在九江和老友重逢,在九江也结识新朋。不管是新朋还是老友,都劝说我在九江置买一套住房,可以退休之后去那里定居。对此,我都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我和妻子家都是修水人,我的儿子孙儿在修水,我的亲戚、同学、同事、朋友也在修水,我的社交圈都在修水,我灵魂之树的根须已然深深地扎入了修水这方天地,如果拔出移走,必然会根枯树死。 相对于出外务工而抛妻别子的人们来说,我们的肉身和灵魂能够合二为一安放在家乡修水,家乡就是我们灵魂的栖居之所,因而,我们是幸福的。而被迫远走他乡的人们,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能够真正使读书和医疗不要自己花费一分钱,并使大家能够在家乡赚到足以过上小康生活的钱财。在城市发展的人们,能够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解决住房问题,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家人团聚在城市,真正融入城市。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在家乡和他乡做出选择,能够使肉身和灵魂合二为一,能够找到灵魂栖居之所。 希望这样的日子不太遥远,期望世间不再有肉身和灵魂割裂之人。 2025年5月19日 周湖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