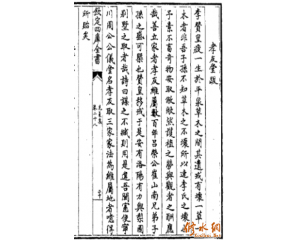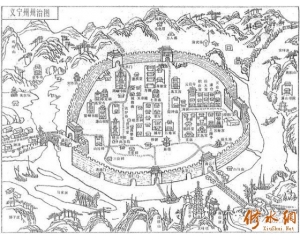|
那年夏天,蝉鸣把空气烤得发黏,我揣着一张没填志愿的纸卡,跟着母亲踏上南下的大巴。车窗外,熟悉的田埂与炊烟渐渐缩小,像被烈日晒化的糖块,最终融进灰蒙蒙的天际。 车是旧的,没有空调,运载五十人的车厢里挤着百来号人,汗味混着劣质烟草气,在三十七八度的高温里发酵。我晕得厉害,蜷在最后排的角落,吐完了胃里仅有的一点酸水,望着前排母亲被汗水浸透的土布衫,忽然觉得这逃亡般的旅程,原是命运早就写好的判书。 到深圳坪山时,日头正烈。车站的水泥地裂着缝,三轮车夫们光着膀子吆喝,空气里飘着炒河粉的油香与不知名儿香水味,和想象中“遍地黄金”的都市相去甚远。小舅来接我们,他穿着沾着机油的工装,嗓门亮得像车间的冲床:“来了就干活,别想那些没用的。” 他在一家模具厂当师傅,通过关系把我塞进车间做学徒。第一个月领工资那天,我捏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突然想起母亲在外面帮人带孩子,也是这个数。那时候觉得,能自己挣饭吃,大约就是成长的全部含义。 车间是另一重世界。铁屑飞溅如星火,机床轰鸣盖过人语,三伏天里车间仅有的几把风扇,也被元老们牢牢的把持着,其他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小舅是这里的大师傅,脾气暴得像随时会炸的氧气瓶,教我认图纸时,铅笔头敲得我手背发红:“眼睛长哪儿了?这是基准线!”我笨,记不住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他便当着车间几十号人的面骂:“猪脑子都比你灵光!”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扫过来,像无数根细针,扎得我后颈发烫。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夜里的车间倒安静。我常在下班后留下来,对着说明书琢磨那些按钮的用处。铣床上的刻度盘转一圈是多少毫米,钻床的转速要调到多少才不会崩刃,这些如今看来简单的事,那时要反复试上几十遍。趴在铁架床上记笔记时,总能闻到手上洗不掉的机油铁屑味,混着廉价肥皂的清香,成了那段日子的嗅觉记忆。 变故发生在一个秋夜。九点多钟,我在铣床上加工模板,左手食指被工件猛地撞了一下。钻心的疼瞬间窜上来,像有根烧红的铁丝钻进骨头缝。跑到水龙头下冲了许久,血还是从指甲缝里往外渗,渐渐凝成紫黑色的痂。那天小舅不在车间,后来才知道他在工业区外的麻将馆“修长城”。我不敢去找他,咬着牙把活干完,回宿舍时,整根手指已经肿得像根红萝卜。 那夜无法入眠,疼得实在忍不住,就跑到工业区的篮球场转圈。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天蒙蒙亮时,露水打湿了裤脚,我终于下定决心去找小舅。他听完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完却骑着踏板摩托带我去看医生。医生掀开我裹着的纸巾,眉头拧成个疙瘩:“怎么现在才来?再晚点指甲就长死了!” 打麻药时,针尖刺进指腹的疼反而让我松了口气。看着医生用钳子把发黑的指甲整个拔下来,忽然想起高考放榜那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很久的烟,烟头堆得像座小坟。包扎好的手指像个笨拙的棉花球,回到车间照样要干活。搬模板时不敢用力,攻芽时怕碰到伤口,小舅的骂声却没少:“磨磨蹭蹭的,等着吃闲饭,等着炒鱿鱼?”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有天夜里,我从枕头下摸出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村里的邮递员辗转寄到工厂的,鲜红的封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学费栏那串数字,像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把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折成小方块,塞进床板的裂缝里,好像这样就能埋葬所有不甘。 也是从那时起,心里生了个念头:要走,但不能这样走。我给自己划了条线:三个月,必须能独立操作所有基础工序。此后天不亮就到车间,对着图纸一遍遍拆装模具;晚上别人睡了,我就借着走廊的灯看教程;礼拜天车间放假,就独自一人进去练手。铁屑烫过胳膊,砂轮蹭破手指,这些都成了寻常事。 满三个月那天,我递了辞工书。小舅愣了愣,没骂我,只是说:“到新地方别毛躁。”后来听母亲说,他跟亲戚们讲:“那么多孩子,就这一个能熬。” 哪是能熬啊,若有半分退路,谁又愿意把“扛着”活成别人眼里的“能熬”。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倒不觉得苦了。就像车间墙角那丛野菊,没人浇水施肥,却在铁屑堆里开得泼辣。那些骂声、汗水、带血的伤口,终究都化作了底气。原来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踉跄,都是为了后来能走得更稳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