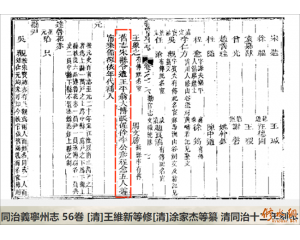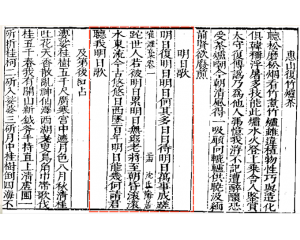|
父爱如山,恩深似海。父亲的恩爱确实深重,“恩爱”,世上只有儿女欠父亲的,没有父亲欠儿女的。而我更是欠父亲的太多,因他为儿女辛苦操劳,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姊妹几个拉扯大,而到老年却没得到什么好的享受,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的父亲名叫“周先伍”,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2009年农历7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他是个苦命人,有人说是黄连苦,他比黄莲苦十分。他从幼年到中年,不知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岁月沧桑和人生坎坷;忍受过很多劳累和曲折,他在默寞时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其实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时不时而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心里就会难受,有时甚至忍不住哭出来。 父亲三岁时丧父,五岁时母亲改嫁于梁,自己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孩子,亲爷爷过辈得早,唯一的依靠只有过继的爷爷。过继的爷爷名叫“周福茂”,他称得上地方的一位武林高手,可惜他没有亲生后代,到中年后才讨个相伴;父亲在无奈之下跟着他过了几年艰苦朴素的生活。 1939年农历8月日军暴行,日军从渣司马往修水方向进功,经过我们这里,当天几架日军飞机在上空转来转去,那年我父亲不到六岁。碰巧他爷爷外出,父亲只好跟着大人们躲进深山树林里去,其奶奶也各顾性命。父亲看到飞机从空中飘下很多的彩色标语,他年小并不知道怕什么,等飞机飞远了就跑出去捡那些标语来玩。不久日军的大部队渐行渐远了,他就一个人先跑回家,见家里房子被日军放火烧着了,他就用脸盆去门前沟里浇水救火;后面还有几个掉队的日兵走来,看见他在浇水救火,那些日兵还摸了他的头,幸好没伤害他;没人照顾的孩子真是可怜。 本文来自织梦 1942年父亲的爷爷去湖北通山县卖猪仔,在茶亭铺附近遇上日军,他以为自己武功了得,就和日军凭手交战,凶狠的日军虽然人多势众,但还是没伤到其爷爷。可是爷爷在逃命中摔伤了身体主穴位,当时走路都喘不过气来,他坚强地逃到茶亭铺附近的一家歇铺里,当夜在那里身亡,就这样爷爷不幸离开人世。相家的奶奶也回了她的原家。后来我父亲像一个尖底的竹篓一样,连放的地方都没有。那年他才八岁,无依无靠的,自己年幼不能做什么事,连饭都不会做,无奈之下,只有来梁家从母亲和继父。母亲看到自己亲生儿子无方可从,就把他带到自己身边,连继父也同意。处在那封建时候,孩子都不能天天闲着的,继父就为他找点活干,免得吃空头饭,别的干不了就叫他帮眏牛。可他在继父和娘亲面前乖巧地生活着,继父见他很听话,而且聪明活泼,却很喜欢。到那两年的时候,继父想把他放去学门手艺,结果托人介绍,就去了修口的一位银匠师傅家学打银子。在旧社会时代,很少有人拿银子去打的,所以空闲时间多,他就得帮师傅家眏牛,不然饭都赚不到吃。在那一直也没什么生意,手艺之事很少有做,因此父亲不到两年就离开了师傅而回到母亲和继父身边来了。  后来,他们召集了各房代表到添福祠开会,还准备了几桌宴席,特地邀请周祝山参加。祝山接到消息就立马坐轿到马祖湖,又叫周澄清和周少梅抬轿送他去溪口,还提前给在其他乡当乡长的弟弟通信,谨防在溪口祠堂发生闹事的现象。据说祝山的弟弟存兵养马。中午,周祝山到了添福祠,看到情况不对竟,得知族长要批斗他,就抽身走人。这时他可想得很周全,他想万一发生什么事来伤害的也是自家人。所以他到快吃饭时,就把饭碗扑放在桌上,说:“今天我做错了事,我把先伍拿给继父做崽是一举两得的事,哪里有错?族长带外地的崽都行;他这个该死的东西,我现在去县里,明天就派人来把他捆到县里去,澄清、少梅备轿,我们走”。说完祝山就坐上了轿子出了溪口街,走到风鼓泉就遇到他弟弟骑马来了,祝山就立即告诉弟弟,你们回去,事情办好了。就这样祝山把快要起祸的火苗踩熄了。其实祝山并没有在县里派人来,只不过是说几句气话,吓得族长躲了三天。后来溪口周氏族人硬是不服气,说要把我父亲带到溪口去归周氏管理会养。有人来信告诉我奶奶,叫我父亲白天不要呆家里,到屋背山上去玩,看到生人僻之,怕溪口人把他带去;那是1948年下年的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些家族主义已被共产党平静下来了,溪口周氏的人再也不敢提起先伍过继之事,就这样我父亲成了周梁两姓各半之人。处在那时代,一个家族有如此的团结,对家族人多么的重要,愿意牺牲一切代价都要保护好每一个族人。希望我们的后代都要向前辈们学习,看重我们的家族,传统美德,团结族人。要理现我们家族的重要思想,先贤裕后贻厥孙谋,子孙秉承绳其祖武。像我父亲这个事类就证明了家族人都是血脉同源的,天下周氏一家亲。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父亲跟我讲的爱家族的故事,更是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家族。 dedecms.com 从此以后父亲就成了康宁的儿子,把“周先伍”的名字改为“梁正宝,号玉珠”,父亲做了康宁的儿子当时心里也很高兴,一个孤儿总算有了个自己的家。可是好景不长,谁知政策巨变,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把康宁划成了富农成份。因反对资产阶级,经常把康宁夫妻俩带去大队学习,父亲做了康宁的继子,也成为富农子弟成份。其实父亲原本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孤儿,因无奈是继立之子,真是有点冤枉,过继给康宁一年就带上了一个成份帽子。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事既如此,何得厌言,大树倒下桠也斜。虽然上级政府公正为民,但地方工作人员想当官做积极分子,就借机办事。因此队里辛苦的事都赖在父亲身上,如挑柴送到大队部,队里用牛耕田耕地等。队上有更苦累的事,别人都不愿去干的就要他去,并不敢推辞。 1958年,大队上要安排父亲去大椿钢铁厂工作,他接受命令,在那辛勤地干了二年。后来又被调到瑞昌钢铁厂,在瑞昌又呆了二年,在厂里任过班长。因继父身体不好要回来照顾,父亲就同在厂的两位同事从瑞昌回到了老家。回来不久,继父因病卧床不起,与世长辞。后来父亲有了二男四女,长男与四女全部姓梁,只是次男姓周,长男九岁时得急性疾病去世。后来把次男改为一半姓梁了,他失去大儿子时心里是多么的痛苦,对他的精神打击特别大。父亲的苦难波灾总是不断,有时还要跟继父去接受学习,耳边还经常听到别人说他是成份子弟。不知怎么命中会注定得这样,他总是自叹自息。 织梦好,好织梦 父亲身单力薄,个子又矮小,身体也不太好,但他走路还行,一天起早摸黑能走百余里,他年轻时去过好多次湖北通山县卖猪仔, 从家里挑担猪仔去一百多里的地方,真是苦得他,我十多岁的时候都看见过他去。他说走长路是第一天看肩,第二天看脚,第三、四天看吃作。也就是说第一天的肩膀会痛,两个肩膀会争着挑担,右肩换左肩,左肩换右肩,到第二天就不太会痛了;第二天的脚会痛,要用裹脚带把脚下部裹紧,到第三天就不会痛了;第三、四天就看吃饭能不能吃得,饭量照样不减;如果这几样不行的话,那你就不能走长路。 父亲遇队里农闲时,还经常挑些农产品去县城卖,如米呀、糠呀、鸡呀、蛋呀、蔬菜等,我家到县城也有三十多里,都是挑担步行的。因为养家糊口不容易,一家老少六七人生活,另外还有人情世故,不去外面换起点零钱来的话,日子真的难过。我记得他总是天没亮就起床,生怕别人知道,队里人晓得的话,又说他去投机倒把,贩买贩卖,因此他回来也是等到天黑才回。我家原来住在一个偏僻的矮山岭上,每当父亲去外面时,一到天黑我就和三姐、妹妹一起站到门前下岭的地方喊着:“回来梦、回来梦啊”,奶奶告诉我们不能叫名字或称呼的,这是前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父亲回来了听到家里人在喊就会回应;“回来了啊”。父亲经过的苦难我只能简单讲述一下,因为他经历得太多太多。他在酷暑炎天不知受过多少署热,傲过多少晌午,流过多少汗;寒冬散雪不知受过多少风霜,遇雪天时甚至穿草鞋带袜绑禾秆绳走路都走过很多;风雨交加、雷云电闪的时候都照样在田间耕作,坚持把劳动事业完成。他为了撑起一个家,披星戴月、百折不挠地是度过他艰难困苦的青春时光,从不叫苦,总是说命里注定的。 内容来自dedecms 父亲的富农成份帽子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摘掉,他是一个最老实的人,从不敢乱讲一句有政治敏感的话,安分守己地过着他平淡的日子。他小时候也读了点书,如增广、幼学、上下论都读过,可是他少年时受了太大的压力和打击,对文学之事全部忘记了。他没事的时候就想起从前那些心酸的往事,总是想着就要哭似的,心却难平,确实悲痛难忍。其实他还隐藏着很多痛苦的事没告诉我们,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家里很穷,房间又少,床也少,我和爸妈睡一张床,有一个深夜,在睡梦中被父亲的哭声吵醒。我一醒来就问父亲,你干么哭啊?父亲边哭边跟我说了很多,那时我年纪太小,说不出什么安尉父亲的话,只是看父亲哭的可怜,自己跟着流眼泪。父亲的苦一直都在他自己的脑袋时隐时现,失眠时他想起那些苦情就哭,他在哭的时候忍不住边哭边说。开始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听完后心里真是难受,我到现在一想起父亲过去的苦难心里就难受。 父亲对为人处世,善德孝道我总是铭记于心,谨将良好家风永传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