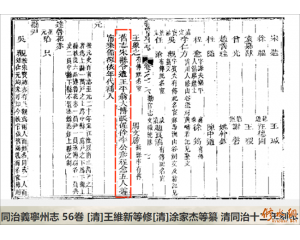|
由于疫情原因,我们过了两个相对清冷的年。今年由于防控政策调整,很多出外务工的亲友现已返回乡里,我似乎又看到了村南村北闹热的气象,眼前便绽放着满天璀璨的烟花。也常常在俗务之余,回想起自己孩提时过年的欢乐往事,它们像春草一样从记忆的泥土里疯长了出来。 那时村子里还没通电,更谈不上看电视听音乐了,自然也不知春晚为何物,可是欢乐却似乎不比现在少呢。 那时候,腊月里天气比现在更冷,老屋瓦檐上长日悬吊着长长的透亮的冰棱。我们一帮小孩子,用竹竿把冰棱打下来玩,渴了就当冰棍吃。老屋地场前面的大水塘里经常结了厚冰,早晨的微暖的阳光照在上面,直晃得人眼睛生痛。往往这时,我们都围着塘子起劲玩闹。将石子瓦片往冰面上丢,赤溜溜的从这头瞬间就滑到了那头。胆子大的狗伢叫我们几个抓紧他的胳膊,一齐使劲将他推到冰面上,他一屁股躺着就溜到塘子中间。可是要爬回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往往他一动身子冰层就发出吱吱的声音,吓得大家喊救命,他却还呵呵地笑。最后,还得大人们扛来竹竿,把他接过来。 临近年关时,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秃顶的大叔便会来炸米花,那可是真正有趣得很的事。他会在老屋上堂前支起火炉,熟练地摆好风箱与米花机。各家叔婆婶子就会用竹升筒量了米呀豆呀苞谷呀来了,还得用箩筐盛点木炭。于是,偌大个平日里空荡荡的堂屋就成了欢乐的海洋。记忆中,每年都是辈份最高的七叔婆第一个炸的,等满头白发的七叔婆颤巍巍的把米倒进米花机的口子里后,秃顶大叔便对着口子吹几口气,往里加点糖精,再用一个小小的猪毛刷子沾点油在铁口子上刷几下,然后把米花机盖子扳锁好,才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左手拉着风箱,右手匀匀摇着米花机的铁柄。火苗呼呼的窜,纺锤形的米花机炉子缓缓地转着,满堂屋的人脸上都漾出笑容。大人们谈笑着,预测着米花炸的好坏;小孩们则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打闹着预备享用喷香的爆米花了。 修水网 约摸过了十分钟罢,秃顶大叔反复地看了米花机上的一个表上的红针针,然后说差不多了,便示意让人把篾篓摆好,把篓后拖着的麻袋捋顺,检查袋底是否扎紧。一切停当后, 小孩子哄的一下远远的捂着耳朵躲开,只有少数胆大的将头夹在他爸或他妈的裤裆里,只露出咪咪着的两个龟眼睛来。只见大叔熟练地从炉火架子上取下纺锤形的米花机,迅速将机子的口子放在篾篓口里,双手握紧把手,用脚一蹬机关,就只听见轰的一声震天响,随着腾起一股白烟,满堂屋弥漫着浓浓的香味。于是,我们又雀跃着围拢来,都扯开衣兜,等着七叔婆把喷香的米花装满一兜,便躲一边美美的吃去。 那时,老屋里住着十多户人家,每家都要炸上几升米呀豆呀苞谷呀什么的,秃顶大叔往往一整天不得闲。在一声声震天响后,在一阵阵飘起的喷香的白雾后,在一波一波的笑声过后,美妙的新年在惬意的咀嚼中渐渐近了。 大年夜终于在我们的热切期盼中到了。父亲半下午就到山上砍了几棵被雪压断的树,把柴劈好。等天色快黑下来,父亲便喊我们兄弟帮着把屋檐下放了半年的大树篼抬进伙房去,他就忙着生火,一时间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和弟弟妹妹挡不过烟熏,往往先跑到老屋场院里放炮仗。其实场院里早就是热闹得很了。一大帮小伙伴早在那玩开了:有的堆雪人,有的放鞭炮,有的捉迷藏,年龄稍大的根伢他们在演练着狮灯,几个小鼻涕虫则擎着草把灯歪歪扭扭的也在练。我们赶忙加入进去,欢声笑语将屋檐上吊着的冰棱子都震落下来。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天完全黑后,各家大人喊叫着孩子回去,场院里暂时静寂下来。我们兄妹进屋,父亲早把火炉烧得旺旺的,红红的火光映在他的黑瘦的脸上显出洋洋的喜气。母亲在灶膛间忙碌着,整个屋子里飘荡着诱人的腊肉的香味。我们雀跃着,兴奋地围着灶台转起来,母亲从砧板上挑出几块刚切好的熟腊猪头肉,逐次塞进我们兄妹三个的小嘴里,我们满足地咀嚼着,那种悠长悠长的香味,至今还回绕在唇齿之间。 吃过年夜饭,小伙伴们就开始相邀着玩闹了。那时没有电灯,各家止点着油灯,昏黄的光晕从大大小小的窗格子里漏出,映射不过一箭之地,便四处是黑漆漆的。唯有老屋祖堂祖宗牌位前点着一对大红油烛,将整个堂屋照得亮堂堂的,那便是我记忆中的天堂了。起先,我们一大伙在根伢与狗伢的带领下,到各家去接果子吃。狗伢是他家里的细崽,五叔公与梅花叔婆当他是个宝,因此也只有他就提着个红纸糊的扁灯笼,把大伙眼红的紧,他却也因此成了队伍头。在他的亮红灯光照引下,我们像一群快乐的鱼儿,游走在黑窄的小巷里。挨次到各家,我们一窝蜂似地说着演练了百十遍的喜庆话,各家叔婆婶子都格外欢喜,都格外慷慨地往我们的衣兜里倒早早准备好的果子。兜完一圈,大伙又回到堂屋,唧唧喳喳地评说着谁家果子更多一些谁家果子更好一些。往往意见不一,不了了之。 修水网 等到四处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小伙伴们陆续的被喊回家团年,新年便也在我们惺忪的睡眼中款款走来…… 这些远去的光阴,如一声声清亮的牧笛,总是敲打着我坚硬的心房,不断提醒别忘记一些温暖。它们每时每刻在我的生命河流里低吟浅唱,为所有的日子增添了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