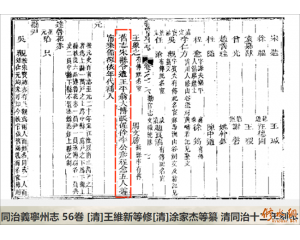|
记得小时候,我们那有户人家,其有四个儿子,都正值壮年,在地方上称王霸道。大家都怕他们。 我们家有一块稻田在他们家门前,稻谷几乎每年都被他们家的鸡吃掉一大半。他们家散养着一大群鸡,有几十只,从来都不关起来的。每每看到他们家鸡啄食稻穗,尽管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也不敢大声的去赶,更不用说敢打了。 没办法,在稻谷快成熟时,我爸妈就派我小两兄弟(当时我六岁我哥八岁)顶个草麦里,拿根棍子去田边守着,不让他们家那伙强盗糟蹋稻谷。 有一天中午,太阳当空炙烤着大地:地上发着白光,田里的水汩汩冒着水泡,泥鳅都大条大条的热死了。我俩的敌人,也全在屋檐下,刨个坑,肚子贴的泥土,嘴喘着粗气,精神萎靡不振,一只只像打了霜的茄子。  xiushui.Net 我和我哥一合计便偷偷跑到附近的河里游泳凉快去了。河里凉快还可以摸捉鱼虾,居然在水里一玩就一个下午了,竟忘了父母交代守田的任务。待明白过来赶到田边一看,我的那个娘嘞!好家伙!几十只鸡正在田里跳脚啄食着尚未成熟的稻穗。 像一伙日本鬼子似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一片狼藉:一根根被吊弯折断,太可恶了!可能吃点倒没什么,只是那该死的鸡,它先跳起来,啄住稻穗吊下来,按在地上,再使劲摆动几下脑袋,如此这般,一根根稻穗,就再无复活的可能了。 被放倒了一大片,叫我俩怎么回家交差哦?气得我哥跳下田里死命的赶。但他还是不敢打,因为他已八岁了,多少是知道一些人情世故的——明白鸡的主人厉害,惹不起。 我就没有他那么通世故了,拿着棍子乱抡一通,只是鸡没有打着,却把稻谷打倒一大片。那家的女主人坐在门口破口大骂我们两个是“少亡鬼”。有两只鸡不知是没把我俩放在眼里,还是鸡仗人势,量我俩兄弟不敢动它们。刚等我们掉转一个身,又跑到田边来啄谷子,还赶都赶不走。 HULING 真是目中无人欺人太甚!气得我一阵乱棍打得它在地上直扑腾。等它勉强逃到它家女主人面前时,结果一命呜呼了。 这下可翻了天。那凶巴巴的女主人捡那只鸡来,对我们又骂又赶,凶得像只母老虎,我哥就跑了。我还不太懂事,楞头楞脑的,还不知道自己“闯大祸”了。心想鸡吃我们家的谷,我们就没有谷子吃就会饿,我打它们没错啊?哪里知道同鸡的战争正义,但鸡的后台主子强大啊! 当晚,那家女主人提着那只死鸡,来到我家,用脚踢开门,要我爸妈赔她鸡并道歉。我爸一脸赔不是的,本打算赔她一只鸡,好息事宁人的,不料那女人嚣张得很!把那只死鸡狠狠地摔到我妈脸上,打得我妈往后一个踉跄差点跌倒。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爸上前推搡了那女的两下;我也冲上去掐了一下她的屁股,也被她踢了一脚。她打我妈我掐他屁股那里解气啊!我本来还想咬她屁股的,却被我爸捏着一只胳膊拉开了。 他还凶我说:“都是你惹的祸!”我好无辜啊!当时觉得我爸是个软蛋。哪里知道他的无奈和苦衷。 内容来自xiushui.Net 我爸就轻轻推搡了她两下。那女的就捂着肚子,就地打滚、哭天喊地的耍起屙屎赖来。 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有这么个耍泼的母亲,她家儿子能弱到哪里去?她小儿子20刚出头,虎头大耳的,嚣张跋扈得很,提着斧子跑到我家二话不说,“咣——咣——咣——”几下,把我家三口锅砸个稀烂,还用指头顶到我爸鼻子上说要打断他的腿。 三口锅被砸了,我妈心痛得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哗哗的掉,心也在滴血!她抱着我的头,虽没有怪我“惹祸”的意思,却无奈的摇头叹息,“崽呀!你做么要惹他们家的人啰?” “我没打他们家人,我只打他们鸡。谁叫他们家鸡老吃我们家谷子。”我帮妈妈擦了一把眼泪说。“蠢仔!打了鸡,就是惹了他们家人。”我妈又擦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挠着脑袋眨巴着眼,一脸的茫然,真不明白打鸡跟人有什么关系。 那年月锅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锅就不能煮饭煮潲。人、猪都得挨饿。那穷乡僻壤的,何况没钱,就是有钱都没地方买吃的,不像现在到处有外卖。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他奶奶的!那家伙真是太缺德了!那怕留一口也好,或是不使那么大狠劲能留个锅底儿,好歹能让我们将就着弄点饭吃,不至于一家十来口人,还有一头老母猪带着刚出生的八只猪崽一起挨饿。 大晚上的,离城里几十公里,且山高路远、黑灯瞎火的,上哪里弄锅去啊。 锅被打了,搞得我家里人心惶惶一片哀嚎!那女人也像个瘟疫一样赖在家里不走。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家里有四兄弟,兵强马壮,胳膊扛不过大腿。 我爸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坐在墙角里抱着头,身体震颤着,嘴里死命地吸着一支烟,只见到他吸进去就没看到他把烟吐出来,鼓着腮帮子,把烟闷在肚子里,巴不得能酝酿个原子弹出来。 论人数吧,我们也有四兄弟。我六岁,我小哥八岁。我虽然参战欲望强烈,而且我胆量也不差:打死了他们家一只鸡,还掐了那女人的屁股。但在我爸眼里,如果真跟人家打起来,我两个是不能算数的,只会碍事绊脚。 内容来自xiushui.Net 我二哥17岁,个顶个可能也算不上一个。我大哥19岁,可能是唯一能派得上台面的人物。可他又不在家,他在离家几里远的师傅家学木匠。 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天注定吧。那晚我大哥碰巧回来了。他看到父亲抱头无奈的坐在墙角里抽着闷烟,母亲泪眼涟涟,锅被砸个稀烂,家里一地鸡毛。还有那个赖在堂屋,哭天喊地耍屙屎赖的女人。 他问清缘由后,气愤得捶胸振脚,血脉偾张,脸上一阵抽搐,攥紧一个拳头使劲的捶在门框上,我感觉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昏暗的灯光下,我拉着大哥的衣角含泪仰望着他说:“哥,我们没锅煮饭了,我好饿!那女人打了妈,还用后腿(后来我才知道人是没有后腿的)踢了我。” 他用手按了一下我的头——示意我走开。我虽然看不清他的脸,却突然觉得他变得高大起来,高大到头都快顶到屋顶了。他一个箭步冲到茅厕,拿起一个尿端,掀开粪池,舀了一端屎尿,劈头盖脸泼到那耍赖的女人身上。 那女人迅速的爬了起来,再也不见她捂着肚子喊痛了,活像一只落汤鸡似的,嘴里骂骂咧咧的夺门而逃了!我大哥又快速从门角提起一把柴斧,冲了出去。 内容来自xiushui.Net 众人都惊呆了,以为他疯了,想赶紧拦住他。哪里拦得住啊?他一个甩手,就往后倒了几个。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跑。只见他冲进那家人的厨房,接着就听到“咣咣咣”三声巨响。震得看热闹的人们都抖了三抖——脑袋都差点陷到脖子里去。随即人群中就一片闹腾欢呼起来。现在想想大抵是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有拍手称快之意吧? 那家人四个儿子,猛地向我大哥冲上去想围攻他。我大哥丢掉斧子,大喝一声,一阵拳脚、左右开弓就干倒了他们中两个。另外两个看到我大哥要搏命的阵势,就偷偷走后门溜掉了。 这时我二哥和我爸也赶到,把打我家锅的那个家伙按在地上“摩擦摩擦”。那家伙太可恨了!居然砸我们家三口锅,害得我晚饭都没得吃。我家黑狗都看不下去了,冲过去挠他的脸,我也跑过去踢他的屁股。 一阵混乱中我被绊倒了,幸好一个就地打滚滚到了一张神台下面,要不十有八九被一帮乱脚踩死了,那读者也就看不到我这篇文章了。 本文来自修水网 当我正要从神台底下爬出来时,由于打斗时神台被弄断了两只脚,一神台的菩萨向我压了下来。我被一个穿花衣的菩萨压得喘不过气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翻过身来,把它拱翻在地。 我气极了!骂它,推它,掐它。它也不还手,还一直微笑的瞅着我,真是没心没肺啊!后来我还不解气,趁大人们不在意时,把它抱回了家,藏在床底下。第二天就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来到我家,拿了一块糖给我,把它换回去了。 后来我稍长大了点才知道,那菩萨是他们姓府上的太公菩萨,平时是供奉在祠堂里的;也是我妈的太公,据说还是一个挺显灵的太公哦。呵呵——真是太冒犯了。我现在每年回家都给那太公菩萨烧纸烧香的。一来是求太公保佑;二来也是算为当年的失敬赔不是吧。 那晚,全村子的人都被我大哥的“英雄”举动惊呆了,拍手称赞:说我大哥厉害!干得漂亮!替他们也出了口恶气。 我大哥平时也是一个挺本分的小伙,没想到那天那四兄弟都能没打过他。我想,这就是人的潜能,兔子逼急了也咬人的道理吧! xiushui.Net 我大哥这一仗对于我家的意义绝不亚于朝鲜战争对咱中国的意义。从此以后都没有人敢轻易欺负我们了。那些鸡都有主人管着了,不敢轻易出来糟蹋我们家田地了。 从那时起我家就年年丰收,再也不闹饥荒了。能吃饱饭,我和我小哥哥也长强壮了不少,而且再也不用守在田边同那些鸡作战了。尤其是大家看我大哥的眼神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 【古城旧梦】出品 微信号:gcjm888888 曹丁山:男,自由撰稿者人。籍贯江西省修水县,长居广东,现经营一家线业公司。漂泊异乡,酸甜苦涩,冷暖自知,空闲时写随笔,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也写诗、散文、杂文,微小说,对一些社会现实叨叨呐喊几声,以表其是一个活体的存在。已在《人民杂志》、《慈怀读书会》、《种园》、《修水报》、《古城旧梦》等平台、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许多文章情真意切,直达灵魂深处,被大量转发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