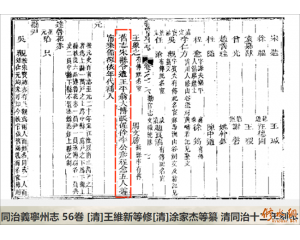|
我是一名当年的上海知识青年。1970年到江西修水县渣津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9月幸运之神就降临到我的身上。黄坊大队革委会决定把我调到黄坊中小学当民办教师。从此,我与教育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一晃,我在教育战线上干了三十七年。其间,我有过彷徨、失落、伤心、痛苦,但更多的是成功后的喜悦。 记得,刚开始教书时,我班有位七、八岁大的小女孩,她有个绰号“北瓜”,当地人把南瓜叫作北瓜,意思是她的脸圆圆的像南瓜。每天来上学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后来,经过家访,我才了解到家里七、八口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大脖子病,即甲状腺亢进。住在离学校较远的山脚下那阴暗潮湿的破泥房里,真可谓是一贫如洗。 那时,我们常常要利用夜晚进行文艺排练,配合政治运动,白天去宣传演出。 我决定重点培养这个女孩,帮她洗头洗澡,换上我为她买的衣物。还自己动手帮她剪了一个童花头。白天,跟着我上课,一起吃饭,晚上与我同睡一个被窝。大家都说这女孩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似的。她也争气,学习成绩优秀,当班长,管理班级大胆泼辣,工作井井有条;外出演出,她报幕、跳舞、唱歌样样出色,特别是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那相当闭塞的大山里令人拍手称好。 内容来自xiushui.Net 1975年春,我要去九江师范进修,离别时,我召集了班里大部分学生步行10里山路到镇上照相馆拍了一张分别合影,一直珍藏着。 离开黄坊中小学的那天,这帮学生以及好多家长、同事,当地的老乡都来送行。当拖拉机起步,带着我即将离开的时候,我哭了,学生们也哭了起来,大人们也都在抹眼泪。拖拉机向前开了,孩子们不约而同跟着拖拉机边哭边跑。拖拉机驶远了,我隐约还看到他们举着小手的身影,我的心都快碎了。 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修水县马坳公社中学教数学兼当班主任。班里有一位身材矮小的男生叫赖波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山区的孩子在冬天通常是一身黑色脏兮兮的棉衣。可他却不同。虽然,也是一身黑衣,但分明十分整洁。上课的时候,瘦削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平时,很少能听到他的声音,神色忧郁。后来,我了解到他的父亲在监狱里劳动改造。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就是黑五类分子的子女,当然抬不起头。 晚上,我失眠了。我感到作为班主任,我有责任要让这样的孩子放下思想包袱,还他一个快乐的少年时代。家庭出身不好,不是孩子的错。再说,在这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我决心帮助他走出阴霾。 修水网 从此,我有意无意地多次与他谈心,讲有关名人逆境成才的故事。课上,尽量为他创设展示才华的条件,培养他当班干部……慢慢地他变了,活泼了,开朗了,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了。接着,我又鼓励他写入团申请报告,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学生方面思想工作做通了,可学校领导审核时,很多人都投了反对票。唯一的理由就是成份不好。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我据理力争,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戴顶什么“帽子”。为了学生的前途,我压根没想那么多。第一批入团的名单里,还是没有他的名字。赖波平流泪了。我的眼圈也红了。我在心里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无辜的孩子!为什么不设身处地为他想想! 在我的关心爱护下,赖波平没有消沉,更加发奋学习。现在,他是农业局的技术干部。 自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后,我们这批人就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实在有愧于“知识青年”这个称谓。站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的我深感底气不足。好在我有幸遇到了从县城下放的教师。特别是陈秀娟、吴咏芳、朱亚玲等老教师。他们待我像亲妹妹一样。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关心我,帮助我,滋润了我的心田。从此,我走上了自学之路,一盏煤油灯常常伴我到深夜。在马坳任教时,我还常利用休息时间骑车十余里上门求教。 修水网 那时,压缩学制,三年初中内容强挤在两年中完成。其间,常要配合政治运动,如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放农忙假等。所以学生学得很费劲,老师教得也很累。课余时分常有学生来问题目。问的最多的是几何题,那时,我常常一手端着饭碗一手在地上作图,帮助他们分析题意。现在想来,那时真的十分艰苦,为了节约纸张,所以常以地当纸。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通过人才引进,我告别了大山,来到了一马平川的鱼米之乡梅堰中心小学任教。 1988年——1989年,我常发高烧,且查不出病因,后住进了上海中山医院。陈文斌校长带了学校的干部开车到医院看望我。不巧,当天我刚出院。于是,他们又想方设法才在上海老城厢,我的娘家找到我。那时,几乎是没有私家电话的年代,通讯联系极不方便。中午时分,当他们一行风尘仆仆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感谢组织,感谢各位领导对我的关爱。 值得一提的是在梅堰,我曾带的那个高年级班,班长叫林芳。我班的纪律出奇的好,每天出操都能做到静、齐、快。令大家刮目相看。那一阵,我常到上海看病,有一次连续请假一周,我婉言拒绝了代课。临行前,我安排好学生每天的学习任务,由班干部负责管理。教导主任朱兆龙老师很不放心。于是,我跟他说,你们可以随时随地去观察。等我看病回来去见领导,他们都笑了,夸这个班带得好。 HULING 由于学校缺乏数学老师,1990年开始,我改教低年级数学。于是,我重新琢磨教学思路,改变教学方法。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朋友很喜欢我,上课纪律可好了。每学期全镇统考,所教班级的成绩一直稳居前茅,并且从不布置回家作业。由于我居住在平望(爱人单位的福利房),当时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都在读小学,天天带进带出,上下班总觉得不便。于是,想调往平望,平望张校长来梅堰视导工作,听完我的课后就答应要我。 梅堰陈校长得悉我想调离的意图后曾多次亲自找我谈话挽留我。并且,请苏州市教育局数学教研员瞿老师以及原吴江进修学校老校长等都来挽留我,令我十分感动。 但,由于每天搭车上下班常迟到早退。虽然,领导、教师都不计较我,但我总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在1993年秋调入了平望中心小学(现平望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