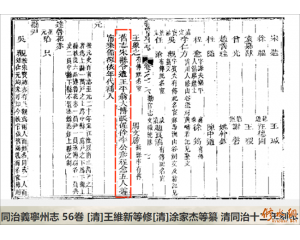|
“我要去洗纱布哩。” 他推托地说。 xiushui.Net 第二天,太阳光果真很好。修水扶我出了门,在门前的小空地上坐下来。阳光象一条条金色的光带,撒满在树林里,各式各样的鸟儿争着在叫。小松鼠在树枝上窜来窜去,有时停下来,对我们呆望了一下,又转身风似地溜得无影无踪,过一会,又在另一条树枝背后探出头来。对面远远的山岗上,两个獐子也在晒太阳。 修水把我们的全部家产——两个小饭包,拿出来,倒出里面的东西,放在太阳光下晒。 他一件一件地翻弄着,突然,他抓住一个小纸包,兴奋地捶着自己的脑袋,嚷道:“啊啊,老吴,你说我该死不该死?该死啊,我这饭包里还有这么一包盐哩,我竟忘得光光的。 他这么高兴,我也就跟着高兴,但还不太知道一点盐又值得产生多少高兴。 “老吴,没有碘酒,用盐水也行的。真的,李医官对我说过,我也见他用盐水给伤号治疗过伤口的。” HULING 我一听代替碘酒的药有了,也异常地快活起来,说:“来,修水,我们再来仔细找找,说不定还会找出什么宝贝哩。” 两个饭包的东西,一转手就翻遍了,能再有什么宝贝!只是我包里有一块擦枪布。前些时候打土豪时搞到一批土制布,差不多有铜钱那么厚。每个红军都发到一块,作为擦枪布。我那块没有用过,还是崭新的。 我望着这块白土布,忽然也有了个念头:“修水,你看,这块布撕撕开,能当纱布么?” 修水摸了一下白布,不自然地笑笑:“用它来敷伤口,好肉也会磨破。唉,太粗太硬啦!” 下午,太阳钻进云堆里了,我就回家去睡觉。不知什么时候耳边响起一阵阵“呼——呼——”的怪声,我细细一听,好象是小刀子在拉紧的布上来回刮着,声音来自门口,修水大约又在搞什么了。 本文来自修水网 “修水,你在做什么?’ 修水跑进来,扬着十分得意的脸色:“我在改造你那块擦枪布呢。” 说着,他把背在身后的手,一齐举在我面前。他的手里,提着一块新的纱布——这是被刮得薄了的那块白土布。 “真难为你了,修水啊!” 我们的生活又愉快起来,我右臂的伤已完全好了,已能够帮助修水做一些轻微的活。我想等臀部的伤口结疤,能走了,那就不愁了,即使左手残废也多少可以做点事吧。 正当我心里充满信心的时候,更严重的威胁已来到我们的家里。 这天黄昏,修水照例煮米粥。起初我还没留意,等米粥煮好,修水不知为什么把大茶缸递给我,自管自拿了小菜缸到门外去吃,平时,我们总是并排坐在床上,边吃边说话的呀。 HULING “修水,天黑了,你躲在门口干什么?” 我喊道,“快进来呀。” “我马上来,” 他嘴里好象塞满了东西,在拚命往下咽。 我奇怪起来,修水一定背着我在干什么,就故意把小瓢丢在地上:“哎啊,瓢掉地上了,修水,给我拾一拾,好吗?” “我马上就来。 可是,他却过了一会才进来,而且空着手进来。他替我拾起瓢,我顺势抓住他,他就在我身旁坐下。 “修水,告诉我,你在门口做什么?” 我低声问。 “吃晚饭哪。” 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借着火炉里的光,看清了他满嘴都发绿,牙齿上还有一小片野菜碎叶。 “今晚吃的什么呢?修水。” “米粥呀!” 修水显然根本不会撒谎,他脸都涨红了,头低了下来。 “你骗我,修水。” 我把他拉得更紧,“修水,把你的菜缸拿给我。”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他望了望我,知道我在想什么了,他头一撇,固执地说:“这是拿大米袋里的米煮的!’ “什么大米袋小米袋的。修水,快把你的茶缸拿来。” “我不,这是上级给你的食粮。” 他顽固极了。 “什么你的我的!快,去拿茶缸来!”我急了,竞呵斥起来了。 “我不… “好,你不,我也不!”我没有办法,假装和他赌气: “你不吃,我也不吃!” 修水见我生气了,有点慌。沉默了一会,他学着大人哄孩子的声音。“老吴,粥要凉了,你快喝吧。我已经吃饱了,真的吃饱了呀!” “我也饱了!” 我有意嘟噜了一句。 他又哄了我一阵,说着说着,哄变成劝,劝又变成哀求: “老吴,你快喝吧……” 修水网 我不能再忍心装下去了,一手扳着他的肩膀,自己也不知怎么地,长篇大论地说了起来: “修水,为什么要分你的我的呢?你在这里,还不是为了我,我牵累了你,我不说,因为我知道你不要听这些。我也不应该说这些,我们都是来革命的,都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对吗?你对我负责,我也要对你负责啊。” “修水,你要是病倒了,不说我的伤口没人照料,你也没有权利糟蹋自己呀。修水,我们都要结结实实地活下去,我们的仇不是都还没有报吗,修水……” 我越说越噜苏,可是心里也越激动。修水静静地听着,牙齿把嘴唇紧紧地咬住。 “你要再说什么大米袋小米袋,就不是把我当自己同志!”我又威胁似地说了一句。 “好了,老吴,不要说了。” 他笑了笑道,“我这就去拿菜缸。 我们分食了这缸米粥,还决定从明天起一天改吃两餐,中午那餐由米饭改成厚粥,晚上那餐一半米粥一半野菜。 本文来自修水网 这样又过了五六天。 早晨,修水背了个空饭包去采野菜,我躺在床上一个人在想,大米袋里的米也剩下不多了,吃完了净吃野菜能行吗?……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队伍身上。 “什么时候同志们能打回来呢?” 我正想得出神,修水气喘喘地奔进来,脸上充满着喜色:“老吴,老吴,我,我听到枪声了。” 我呼地坐了起来:“在哪里?在哪里?” “很远,在山下。”他用衣袖抹着额骨上的汗水:“一定是我们的队伍打回来了,一定的,一定的。” 白匪不会无缘无故放枪,但真的是不是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还不能断定,怎么办呢? “我到山下去一次!”修水决断地说。 本文来自修水网 唉,我这该死的腿虽然已可以走动,但还是一拐一拐的。拐着腿下山,不说要四天也得三天,到山下说不定同志们又转移了。让修水一个人去,我怎么能放心?他到底还是个孩子啊。 “我到山下去一次,好吗?老吴。” 我望望他:“你一个人下山?” “嗯哪,一个人。”他点着头,“我算过了,我们上山走了四天,那时你刚受伤,我们走得慢。现在我一个人走,又是下山,比上山快,最多一天一夜,就到山下了。如果真的是同志们回来,那就好了,要不是,我也要想法带点吃的回来;还有盐,我们都剩得不多了。回来算它走两天一夜,最多三天工夫,我一定能赶回来的!” 他一个人走这么远,我怎么也不放心。修水见我没吭气,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觉得蒙受了莫大的侮辱,激动得眼眶也湿了。“老吴,你,你不相信我?怕我……” “不不,修水,不不,好同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我觉得自己的眼眶也湿了,“修水,我只是为你担心啊!”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然而,不去也不行,我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既要去,他就要立即动身。我就逼着他把米袋拿出来。米袋里剩下的米,照我们目前的吃法,还能维持一个人吃五六天。我就留下三天的米粮,剩下来的,逼着他煮好两茶缸米饭,把米饭捏成团,包好,放在他带走的饭包里。 “修水,你就放心地去吧,米粥我自己完全可以煮了。”我伸出长好了的右臂,又拍拍腿。 “这包烟,抽三天尽够了,只是野菜还要去采一些……” “我自己会去采的,不信,我走给你看。” 我说着就要下床来,他急忙阻止。 “不要看,不要看。我想还是——” 他想了想,“我现在再去采一些来吧。” 我一把抓住他:“要走,还是马上就走吧,修水。” 一切都准备好了,修水又给我换了一次药。他又给我找来一条很合适的树枝当拐杖。最后,他取出那两个手榴弹,分一个给我:“老吴,我去了,你要自己小心,我三天之内一定回来!” HULING 太阳光照进我们的棚子,修水起程了! 我拄着拐杖,一直走到山坡的尽头,望着他渐渐消失在树林深处的背影。 修水下山去了,他带去了我半爿心,在另一爿心上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白天,我不想吃米粥,、晚上,我睡不着。 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天黑了,我就生起火,坐在篝火边,想着修水,他现在到山下了吗?天亮了,我就撑着拐杖,走到对面的岩石上,遥望着…… 又是一天! 第三天终于盼来了,我照例坐在那块岩石上,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暮鸟投林。修水还没有回来,山谷渐渐地暗淡、模糊了,树林也安静下来,四周一片沉静,我只听到自己的心的跳动。 突然间,一个遥远的声音,梦幻似地传来,里面似乎还夹着我的名字。 内容来自xiushui.Net “老吴——我回来了——” 我的心猛然震动,接着就怦怦地一阵乱跳,象要跳出胸膛。 山谷也在喊:“老吴——我回来了——” 修水,是修水,是他的声音,是他在喊! 我骤然站起,把全身的力量都推涌到嗓子里:“修—— 水——我在这里! 修水回来了,他背着一个大包袱,挎着一个大饭包回来了! 我把篝火添旺,让修水放下大包袱,取下大饭包:“不许你说话,先休息五分钟。” 他笑了,我也笑了。虽然没有表,我还是相信我们都没有等满五分钟就憋不住了。他说了:“老吴,我见到参谋长,还有侦察科长。可惜侦察连又先出发了,没有见到。”我迫不及待地问:“队伍住下了?” “没有。” 他摇了摇头,“我下山时,部队正睡得香哩。参谋长听说是我,连忙起床。他说,天一亮部队就出发。他还叫我告诉你,不出一个月,准回来,那时候,这一带就要重新成立苏维埃哩。” xiushui.Net 火光映着修水的脸,他的脸象一个熟透了的苹果,“参谋长叫我们耐心等一个月,不,不用一个月就行了,老吴,你来瞧,参谋长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他解开大包袱,一样一样地说着:“这是大米,这是一块腊肉,这是一块猪油,这是一包斑椒干。晤,” 他又忙抓过饭包,快活地嚷道:“这回,不但纱布充足,还有一大盒美国药膏哩,美国鬼子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没想到东西到我们手里来了。” 我望着这一大堆东西,心里却仍在想着修水。这么多东西,他背着爬了两天一夜的山路,我情不自禁地说: “修水,你背了这么多东西,太累了!” “不,不,”他急忙摇头,“我没累着,真的。参谋长派了两个同志送我的。本来这两位同志也要来看看你,因为怕拉下队伍太远,赶不上,今天早晨我们分手的——呀!”他说到这里,突然一声喊:“我把顶重要的事忘啦!"说时,从饭包里摸啊摸的,摸出一个半块肥皂大小的小纸包。那纸是一种不透水的油纸,我想一定是很名贵的东西了。 HULING 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硬硬的、黑里带黄的东西。修水高兴汉了地笑着说:“这是侦察科长在一个土豪家没收来的,说是一种很贵很贵的外国烟丝饼哪!参谋长叫我带给你。” 我拿起来放在鼻子上嗅嗅,一股涩中带苦,苦中带香的味道,直冲脑门,舒服极了! 修水回来了,我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再不用吃野菜了,而且,还有斑椒和腊肉。我们还有真正的纱布和药膏。 修水回来了,天气也越来越暖和,冬天已将完全过去了。我的腿伤收了口,我已可以和修水一同到森林里去散步,到山坡尽头的岩石上去坐坐,遥望在对面山岗上闲步的獐子、黄羊,还有那盘绕在山谷上空的苍鹰,和那浮动在高高的蓝天上的白云。 映山红从草丛里钻出来,爬满了山坡。白色的野丁香也紧跟着从岩石缝里探出身子。野紫藤给老橡树穿起一身紫色的新衣……深深的山谷,隐隐地在呼应着布谷鸟的歌声。 春天来到了幕阜山;我们的幕阜山哟! HULING 当红十六师回到修水、平江一带,建立苏维埃时,我的伤口基本上好了。参谋长派了人来把我们寻找回去。到军区的第二天,我奉命留在军区。修水随着连队奔赴前线去了。 临走时,我握着他的手说;“修水,我等着你打了胜仗回来。” 修水用力握着我的手,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一定都能为革命立功的。老吴,庆功会上见!” 本文来自修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