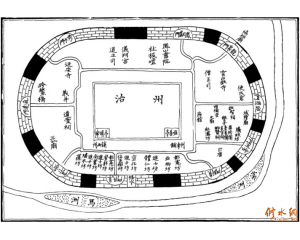当铺不大,巷子却因它才叫了当铺巷。在义宁州人的眼里,它不叫当铺巷似乎就再也没有别的名字可叫了。正如州城里的另外一条小巷,因了一个铁匠铺才叫了铁炉巷。当铺的门面虽小,威严却是天生的。九级花岗岩的台阶,一级比一级高,一级比一级阔,甚至比县衙前的那几级台阶还来得凶猛,来得彪悍。门口立了两个石狮子,块头不大,却是筋骨毕现,目光炯炯,不啸而怒,不眦而威。普通的汉子倘若落脚在台阶上,见了那石狮子,形体早就畏缩了三分。当铺的门面甩脱不开,那门口自然也跟着狭隘了,又一扇厚实盈尺的木门挡着,倘若横了门闩,纵有万顷的气力,恐怕也只是蚂蚁撼大树,自不量力。墙是夹层的,九寸宽的青砖两排并在一起,直砌到了墙顶。四围的风火墙极像了一只簸箕,高高翘耸着,将小巧的一个铺子贴在胸口上。谁也夺不走,铺子也挣不脱。
 本文来自修水网 当铺是义宁州城唯一的当铺,独占的买卖,它不像一般的店铺那样愁着营生,只要开了门,典当的生意便断不了。当铺的主人因此活得滋润,从容,如闲鱼戏水一样自在。当铺的伙计也跟着得了闲,日上三竿开门,日垂天边闭户,比普通店铺的伙计多歇了半天光景。这当铺传到赵半窗手里,也不知历经了几世几劫,反正赵半窗的日子生来就这么笃定,闲适。一张太师椅,一盏水烟筒,一杯碧罗春,赵半窗就那么端坐于柜台后,吸一口烟,品一杯茶,眯半会眼,四十五个春夏秋冬就那么打发了,只是鬓角不经意间被烟雾缭绕了几丝沧桑。赵半窗多半时间局仄在当铺内,那么不咸不淡地生活着。偶尔他也会趁着晨曦或黄昏,在当铺巷走上一个来回。当铺巷人见到的赵半窗总是一袭长衫,一页纸扇,满脸淡淡的笑容,不紧不慢的步子,镇定而又散淡,和蔼而又有种说不出的威严。 当铺的伙计是个老伙计,一般物件的鉴定估价只在股掌之间,有时甚至比赵半窗还拿捏得细微,用不着赵半窗花费什么心思。只在一些年代久远的字画上,老伙计才会犯些迷糊,也只有这时候,赵半窗才会瞄上一眼,吐几个字,铁下一个价格。话出了口,余下的事赵半窗就不再理会了,由着老伙计侍候。赵半窗有他赵半窗的规矩,该他说话的时候说话,不需他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也不多说。祖辈的规矩多,到了赵半窗手头上规矩就少了,少了规矩但不等于没有了规矩。赵半窗有三条规矩老伙计是烂熟于心的,一是一钱不文之物不当,二是来历不明之物不当,三是活人不当。犯着此三条的,没有谁可以勉强赵半窗。除此三条,赵半窗什么生意都接,什么活儿都揽,还真没有一件活计砸着手的。 修水网 而这世界似乎总是矛盾着的,有了规矩,破坏规矩的人就会存在。赵半窗的规矩差点就坏在丘八身上。这丘八不是当铺巷的,可他老是往当铺巷跑,好像当铺巷里谁欠着他什么似的。事实上也没见丘八扰着谁,他来了当铺巷哪也不去,就往赵半窗的当铺里钻。不过丘八在当铺里也呆不了多久,马上就出了铺子,一溜烟往州城的繁华处去了。丘八隔三差五就会在当铺巷出现一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丘八是来当东西的。也许是丘八尝着了当东西的甜头,有一天竟然扛了一个死人来当。那死人是从州河里捞起来的,丘八和着州城里的几个所谓好汉抬了它放在当铺的台阶上。丘八拿手指着老伙计说,你去告诉赵爷,这死人值一百块银元啦。那老伙计哆哆嗦嗦进了里屋,不过半盏茶的功夫,赵半窗就拧着眉头铁青着脸走了出来。丘八又说,赵爷要是不当了它,那就暂时寄存在当铺里,等我们寻着了买主再来取。赵半窗扫了一眼那几个好汉,那些人碰着了赵半窗的目光也不躲闪,脸上嘻嘻笑着,都是同一种表情。赵半窗说,这事好说,不就是一百块银元么。我们来打个赌,要是你们赢了,就是一千块银元我也给你们,要是你们输了,你们该把它抬哪就抬哪去。丘八听赵半窗说到赌,眼睛里早放出了光,说,赵爷爽快,爷们好的就是个赌,但不知赵爷怎么个赌法。赵半窗从腰眼里摸出一把刀子,像柳叶一样小巧的刀子,闪着幽幽的冷光。赵半窗将刀子给了丘八,将平常用的白银水烟筒顶在了头顶,说,你们几个轮流用刀子扎,扎落了水烟筒,你们就赢了,扎不落你们就输了。丘八握紧了刀子,说,赵爷,这可是你说的,刀子可不长眼睛。赵半窗说,扎吧。丘八的手却莫名其妙地抖了起来。旁边的那几个好汉见了丘八的犹豫,一个劲地催促,说,快点扎呀,你不扎让我们来扎。丘八的刀子抖抖颤颤地出了手,落在了赵半窗身后的门柱上。丘八脸红脖子粗地站到了一旁。后来那几个好汉轮流着扎了,有的刀子从赵半窗的头顶飞了出去,有的扎偏了仍插在门柱上,还有的直接落在了台阶上,当的一声响,反将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有一个胆儿特大,直望着赵半窗的脑袋扎了去,赵半窗一张嘴,竟然将刀子咬着了。赵半窗笑了笑,对呆若木鸡的好汉们说,你们输了,轮到我来扎你们了。赵半窗将水烟筒递给丘八,丘八的双手反扭在背后,怎么也不伸出来。赵半窗却不管这些,将水烟筒往丘八头顶上一搁,朝后退两步,捏了刀子就要扎。刚才还嚷嚷的几个好汉禁声了,一个个站往了旁侧里。丘八笃的一声跪下了,说,丘八有眼不识泰山,赵爷饶了我。赵半窗并不接话,扭身径往当铺去了。丘八同了那几个所谓的好汉抬了尸体,灰溜溜就要走。赵半窗在铺子里说,慢着,就这么走了。丘八他们又直楞楞地站住了。赵半窗捏了几块银元出了屋,说,买一口薄木棺材,把人给葬了。余下的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钱。丘八从赵半窗手中接过银元,满脸赤色地走了。 内容来自xiushui.Net 丘八原是九曲巷的,他祖父凭着一身力气和胆识,成了州河船队的头儿,数十年风口浪尖的拼搏倒是挣下了一份不薄的家业。可轮到丘八,什么也不愿干,什么也干不成。如果只是坐吃山空,丘家原也可以支持些时日的,无奈丘八嗜赌,白天赌晚上也赌,桐油燃尽了就拿肥肉做油烛,赌过来赌过去,一份家当慢慢就散尽了。他父亲被噎得一口气接不上,蹬腿伸胳膊赴了鬼门关。丘八家里只剩下一个婆娘,少了拘管丘八越发放肆了。家里的银元没了,丘八就开始当东西。那时候,丘八想当铺真是一家好铺子,不管拿了什么都可以换到锃亮的银元。丘八就频繁出入当铺了。刚开始的时候,当铺巷人见丘八空着手来,又空着手去,后来值钱的东西没有了,就搬箱抬柜,抱瓶捧罐,什么物什都拿了来,走的时候仍是空了手走。 丘八来的头几回,都是老伙计接待的,赵半窗偶尔也见着一次,只像往常一样并不言语,见了和没见着是一个样。赵半窗对丘八根本没什么印象。典当是极不等值的,丘八难免有些不服气,可不服气又能怎样,爱当不当,老伙计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最后丘八只得屈从了。丘八心底里算计,反正马上要赢回来的,无非是费几个铜子的利息而已。然而,丘八的赌运实在不佳,那些活当的东西慢慢变成了死当,全改姓了赵。也许是丘八输红了眼,后来竟然掖了一尊小巧的金菩萨来当,那菩萨是立着的,坦胸露乳,好像手中撑了一根篙,老伙计觉得稀奇,就给了赵半窗。赵半窗接过手,仔细端详了一番,认得是义宁州河船帮敬奉的船神。这丘八该是船帮丘老大的后人了,赵半窗想。那一回,丘八拿到了二百块银元。赵半窗也因此记下了丘八,一个瘦削而苍白的赌棍。 HULING 还有让赵半窗记忆犹新的是丘八的女人红烛。红烛之所以来到当铺,是因为要赎回丘八典当出去的东西。红烛往往在午后进入当铺巷,那时候阳光还很炙热,人们都龟缩在自个的巢窠里,街市上少有人走动。红烛一个人寂寂寥寥地行走在铺满小青石的街面上。她的眼睛始终盯住地面,只在快到当铺的时候,才会像蚕吐丝一样把目光朝四围绕一周。之后,红烛迅速上了台阶,背影随之掩没在门扉里。红烛的脚步是软绵无声的,她的到来并没有惊醒迷糊的老伙计。红烛必须轻轻地唤叫几声,老伙计才会从美梦中脱身而醒。然而,红烛的赎买是徒劳的,她箱角里的几个私房钱有如杯水车薪,甚至衍变成了对丘八的一种怂恿。很快,红烛的怀里只能摸出几个铜子了,而这几个铜子不过是她替人浆洗了三天衣物的工钱,连一件最廉价的典押物也赎不回了。寂静的阳光,寂静的午后,红烛怀揣了几个染了绿锈的铜钱,沿着来时的道路软绵无声地出了寂静的当铺巷。 红烛频繁进出当铺巷的时候,赵半窗正在院落里午休,偌大的院落里只有桂花树上一两只蝉在鸣叫,那条看家护院的狗也卧在树荫里,像他的主人一样悄无声息。赵半窗的睡梦是隐晦的,也是朦胧的,有过风花雪月,也有过实实在在的女人。可赵半窗并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人,他的春花秋梦同他的婆娘有着莫大的关系。赵半窗的婆娘不聋不哑也不瞎,在当铺巷里还称得上是个美人。可这个美人随了赵半窗不到一年就瘫痪了,吃饭撒尿拉屎都在同一张床上。整整十五年,赵半窗没有一天不替美人擦洗身子,端屎倒尿。后来还不得不请了个老婆子帮忙料理。这样的女人赵半窗有理由休了她,也有理由另外找个女人,可赵半窗没有,赵半窗只是偶尔在梦里有过身分不明的女人,有过同身分不明的女人做着同美人一起做过的事。当然,那个身份不明的女人绝不可能是红烛,因为那时候赵半窗压根就没见过红烛。更不用说梦见红烛一个人落寞地走出当铺巷。 修水网 赵半窗之所以能够见着红烛,完全是因为一对翡翠镯子。那镯子扁平如韭菜叶,上面却刻了凤凰和鸣的花纹。老伙计从丘八手中接过镯子时轻轻碰了碰,那悦耳的乐音立刻萦绕在铁栅栏间。老伙计随之开出了三十块银元的价码。他妈的,才值三十块。丘八的骂声从铁栅栏外泼了进来。也许是丘八的骂声惊着了,也许是和鸣的乐音唤醒了,赵半窗恍然如悟,说,把镯子拿过来让我瞅瞅。那对带着红烛体温的镯子经过老伙计的手很快就传到了赵半窗的手上。赵半窗迎着光线将镯子举过了头顶,他的头顶立刻现出了两道盈绿的光环。镯子被轻放在桌子上,赵半窗的眼睛看住了丘八,说,死当还是活当?丘八说,管它活当死当,哪样钱多哪样当。赵半窗说,死当八十块,活当嘛,就只有三十块了。老伙计睁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赵爷说出的话。那一次丘八拿走了八十块银元。老伙计寻思着,赵爷是往水里扔了五十块银元,连个响声也没有听着。 赵半窗是喜欢上那对翡翠镯子了。原想着给床上的女人戴了,可女人这么多年卧在床榻上,手腕不知不觉粗壮了,根本套不上去。女人脸上莫名地有了愧疚。女人是无福消受了,赵半窗叹口气,将那对镯子锁进了抽屉,将一份凄美的怅惘锁在了心里。 红烛再次出现在当铺巷纯粹是为了那对翡翠镯子。那对镯子是她娘给她的陪嫁物。后来,她娘死了,只剩下一份不尽的纪念套在手腕上。可这份纪念也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丘八强行撸了下来,典当的银元又化做了骰子的抛物线,一起一落之间全没了踪迹。这一次,红烛并不是想赎回镯子,即使能赎回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丘八再一次将她强压在门槛上,再将镯子从她的手腕上撸下来,再典当出去,再去抛那的溜溜转动的骰子。红烛什么也不想赎买了,只想看一眼那曾属于自己的镯子。红烛靠着柜台小声问,那对镯子还在吗?老伙计明知故问,什么镯子。红烛说,就是丘八典当的翡翠镯子。你想赎回去?那是死当的,你想赎也赎不了。老伙计瞥了她一眼,转身从墙壁上取下了鸡毛掸子。那看一眼行么,就看一眼。红烛的声音里满是乞求。那有什么可看的。红烛嘤嘤地哭了。你哭也没用哦,镯子不在我这儿,我想给你看也给不了。老伙计挥动鸡毛掸子在柜台上扫了一把,眼睛也像鸡毛掸子一样在柜台上扫了一把。红烛彻底蔫了,靠着柜台的身子像一株经受了风霜的野草一样直往下萎,一直萎到了柜台下的泥地上。老伙计不得不把赵半窗请了出来。 内容来自xiushui.Net 那一段时间,赵半窗常倚在桂花树下的躺椅上做梦。他的梦里有一双手,像柔荑一样柔若无骨的手。那双手赤裸裸地伸在他的眼前,好几次赵半窗都想捉住那双手,但结果都没能捉住,那双手突然从他眼前消失了。自从得了那对翡翠镯子,赵半窗几乎每天都是从睡梦中怅茫地醒来。醒来后,赵半窗免不了会把镯子拿出来不着边际地瞎想一番,那个戴过翡翠镯子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有着像柔荑一样柔若无骨的手,有着像十五年之前美人的模样。赵半窗的想象永远停留在一片虚幻之中,总也凝聚不了具体的形象。老伙计叫唤的时候,赵半窗睡得正酣,他又梦见了那双手,这一回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想着要怎样才能捉住那双手。甚至赵半窗连那双手也没仔细看,他的目光正沿着白晰的手臂往上爬。他很想看清楚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么一双手。然而,那双手臂像是一条迢远的道路,始终没有尽头。在老伙计赵爷赵爷的轻声召唤中,赵半窗再次遗憾地醒了过来。赵半窗的心中微微有些不快。 赵半窗终于见到了翡翠镯子的主人,一个叫红烛的女人,他的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红烛畏缩在高高的柜台下,她的样子很像一只抱紧了身子的刺猬。赵半窗的步子很轻,并没有惊着红烛。红烛依然埋着头在啜泣。赵半窗不得不轻轻咳嗽了一声。红烛的身子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啜泣声止住了,头随之仰了起来。那是一张憔悴的脸,脸上满是斑斑泪痕,可泪痕毕竟遮掩不住她的俏丽。她的目光是暗淡的,却有一丝乞求的光落在赵半窗的脸上。赵半窗说,你是想看镯子么。红烛点了点头,眼睛里乞求的光芒更炽烈了。赵半窗见不得这种乞求的模样,尤其是一个女人几乎半跪在地上的乞求。赵半窗将镯子摊在手掌心里,示意红烛拿过去。红烛却一动不动,眼睛痴痴地盯住那镯子。那对镯子就像两瓣绿盈盈的月亮,在赵半窗的掌心辉映出无限的光芒。 本文来自修水网 后来,红烛的手终于抖抖颤颤地伸过来,捧起了那对翡翠镯子。赵半窗也终于寻着机会一睹曾戴着镯子的那双手。那双手彻底被日常的生活给毁坏了,掌心老茧密布,没有一丝白嫩的颜色。这双手同赵半窗梦里的那双手有着太遥远的距离。赵半窗的心里有几分沮丧。赵半窗似乎忽视了掌心之上的手臂。当红烛撩起袖子将那对翡翠镯子套在手腕上的时候,赵半窗的心情才有了好转。红烛的手臂的确像赵半窗梦中的手臂一样的白嫩,像柔荑一样柔若无骨。赵半窗很想握一下那双手臂,可终究没动,甚至他的目光也没有长时间停顿在那里。赵半窗问,你是专门来看镯子的么。红烛使劲地低了低头,然后捧着那对翡翠镯子再次嘤嘤地哭了。赵半窗说,别哭哦,镯子好好地在这里,戴上让我瞧瞧么。戴上让赵爷瞧瞧哦。老伙计也在一旁帮着腔。红烛含泪把镯子套在了手腕上,那双手似乎更柔媚了。赵半窗的心也像套了镯子一样柔若无骨了。赵半窗说,镯子对你那么重要,你拿回去得了。赵爷,镯子可是死当的呀。老伙计又插话了。不就八十块银元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赵半窗乜斜了老伙计一眼,老伙计立刻敛声息气了。不,不要,我能看一眼就满足了。红烛慌忙从手臂上摘下镯子,双手捧还了赵半窗。还了镯子又添了句话,谢谢赵爷。赵半窗说,不谢不谢,看一眼又掉不了什么,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本文来自修水网 那个叫红烛的女人走了,赵半窗看着她抬脚跨出门槛,然后迈着细碎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出当铺巷,消失在巷口的朦胧处。此后红烛再也没有来过当铺巷,似乎永远消失了。赵半窗让老伙计将躺椅搬到了柜台内,除了吃饭睡觉,赵半窗从不离开柜台半步。赵半窗似乎在渴望着什么。然而,赵半窗越是渴望,那个叫红烛的女人越是不见影踪。赵半窗只能在心底一次次回忆那张憔悴而又不失俏丽的脸,回忆那翡翠镯子套住的双臂,回忆红烛抬腿跨过门槛时的姿态。赵半窗还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一个女人。 赵半窗被渴望燃烧的时候,红烛正在另外一个院子替人浣洗衣纱,努力地挣着那几个锈迹斑斑的铜子。而丘八呢,因为当了翡翠镯子,手头突然阔绰了起来,在赌坊吆喝的声音也特别亢奋。然而,十赌九诈,丘八总也无法戡破其中的机关,八十枚银元很快就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流向了别人的怀抱。丘八始终在上游,而别人总是在下游,水总是不可遏止地往下游流去。当最后一枚银元押上去化做一串吆喝的时候,丘八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赌桌,猴到了一个灯光照射不到的角落。丘八的脸是死灰的,心也是死灰的。他就想那样在角落里突然结束了自己。如果丘八真的结束了自己,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可能再发生了。问题是丘八根本不想结束自己,丘八要扳本,丘八要把自己输出去的钱全赢回来。丘八的希望是在下半夜的寂静中浮出水面的,他终于说服了一个熟识的赌徒,借到了二十九块银元。丘八正好二十九岁,二十九块银元恰巧是他的幸运数。事实上二十九并没有成为丘八的幸运数,相反却是他另一重劫运的开始。眨眼之间,那二十九块银元又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在丘八苦苦哀求下,又一个赌徒借给了丘八二十九块银元。可惜的是这一个二十九也没能给丘八带来好运。借了赌,赌光了再借,丘八终于跳入了赌徒们精心设置的陷阱里。又一个夜晚过后,连丘八自己都记不清借了多少次银元,只知道那些锃亮的银元就像蝴蝶一样忽闪忽闪飞走了。走出赌坊的丘八一脸死灰,他已经欠下赌徒们八百多块银元了。 本文来自修水网 丘八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州城的街市上。八百多块银元就像八百多块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上,丘八连呼吸都觉着困难。丘家的院落早已抵了赌债,只剩下二间破旧的草房,根本值不了几块银元。除了女人红烛,丘八什么也没有了。想到红烛,丘八的眼睛亮了亮,马上又暗淡了下来。丘八彻底绝望了,天要灭丘八么,丘八哪能活。丘八的确是没有活路了,他寻了根草绳系在横梁上,横梁很矮,丘八捡了几块石头垫着脚板,头往上一挺草绳就套住颈脖。可惜草绳已腐旧,根本承受不了丘八的重量。草绳断了,丘八咚的一声掉到了地上。那几个逼债的赌徒气势汹汹地冲进草房时,丘八正歪头耷脑瘫坐在泥地上。其中一个长了一脸横肉像屠夫一样的赌徒跳过去扣住了丘八的衣领,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死了还不如死只狗,死只狗爷们还有肉吃,不还银元,想死有那么容易么。那爷们话音未落,一掌早扇在了丘八的脸上,丘八的半张脸立刻肿胀了起来,气鼓鼓地像个地瓜。 红烛在赌徒们等待的耐心熬到极点时回到了草房。红烛替人搓洗了一整天的衣物,已是满身疲惫。红烛的疲惫并没有消减她的美丽,相反软绵绵的姿态惹来了更多狼性的目光。红烛乜斜了一眼那些男人,就再也不做声了。红烛明白,肯定是她那个不争气的男人又欠赌债了。红烛懒得去理会他们。红烛的漠然似乎激起了赌徒们的愤怒,那个像屠夫一样的爷们又拎起了蹲在地上的丘八,说,你去同你娘们说。丘八几乎是跪着爬到了红烛的跟前,他搂住了红烛的双脚,未说话到先有了哭声。丘八说,红烛,你救救我,替我还了这笔赌债吧。红烛的身子僵硬在那里,她的双脚被箍住,怎么也挣脱不了。红烛的内心像有一把火在炙烤着。我哪有钱替你还债,你去卖房呀,要不连我也一块卖了。红烛的声音尖锐成了愤然的呐喊。嘿嘿,你还真的说对了,爷们就看中了你这张脸。那个屠夫踅了过来,嘴上嘿嘿笑着,突然探手在红烛脸上拧了一把。红烛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两团红印。红烛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全唾在了屠夫的脸上。红烛说,你做梦去吧,就算我变了鬼,也要噬死你。屠夫却不恼,用手抹了一把脸,弯腰揪住丘八,像钵儿一样的拳头一拳一拳落在丘八的胸口上。丘八先是哭爹喊娘的叫唤,后来变成杀猪似的嚎叫,再后来矮了声息,有一声没一声地吐着几个字,红烛,救救我吧,救救我吧,红烛。丘八的声音足够凄惨了,然而红烛却没有理会丘八,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红烛的目光罩在那几个凶神恶煞的赌徒身上。红烛说,你们爱怎么捣弄就怎么捣弄,千万别手软,死了就干净了。听红烛这么说,那几个赌徒相互对视了一眼,竟然住了手。其中一个瘦猴模样的赌徒用手掌拍了拍丘八的脸颊,说,听听你娘们说的什么话,她恨不得你死了哇,你还把她当宝贝藏着掖着。丘八突然从地上弹了起来,从灶台上抢了那把薄铁皮的刀,一蹦一跳就到了红烛的跟前。丘八将刀卡在红烛的脖子上,他的眼睛里逼出一道血红的光。丘八说,你不替我还了赌债,我一刀了结了你。红烛却是一点也不惧,仿佛搁在她脖子上的不是刀,而是一根项链。红烛的话也很从容,她说,有种的你就砍呀,你拿刀逼着自己的女人,你真像一个男人了。丘八似乎被红烛的话噎着了,只说了一个字,你。丘八真就闭上了眼睛,将刀举过了头顶。丘八的刀来不及落下来,就被那个屠夫击落了,刀掉在地上当啷一声响。屠夫又一掌扫在了丘八脸上,说,你真想砍死她,叫我们人财两空呀。后来屠夫一把箍住了红烛的手,死拉硬扯着往外拽。红烛低头一口咬在那只拉扯她的手上,那只手立刻现了一排牙印,牙印里很快涌出了血。屠夫扬起了那只带血的手,却久久没有落下去。屠夫说,我还真舍不得扇你呢。屠夫再去拉扯红烛的时候,红烛的手里多了一把刀,那把丘八扔在地上的刀。红烛把刀横在自个的颈脖上。红烛说,你们做梦去吧,我就是把自个卖给千千万万的男人也不卖给你们这群畜生。屠夫的手终于重重地落在了红烛的脸上,红烛的脸歪扭了,五个血红的指印烙在了那里。屠夫说,你去卖呀,看你能值几块银元。别给脸不要脸,我看哪个狗日的狗胆包天敢要你。去呀,你去呀。红烛真就昂首挺胸地出了门。 HULING 九曲巷的阳光是灿烂的,那种灿烂的阳光将红烛笼了一身。阳光里的红烛有过短暂的迷惑,但她很快就清醒了。红烛抬头望了望天空,天空一片纯净的蔚蓝。透过那片蔚蓝,红烛看到了翡翠镯子绿盈盈的光芒,看到了赵半窗慈善的眼睛,甚至她还看到了赵半窗眼睛里的朦朦胧胧的渴望。红烛终于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了。 那些日子,赵半窗要么睡在躺椅上,要么端坐在八仙桌边。老伙计觉着赵半窗似乎变了,但就是说不上哪里变了。赵半窗的心是深沉的,似乎没有人能够从他的外表上看出什么,连老伙计也猜不透他的所思所想。自从红烛看过翡翠镯子以后,赵半窗一直将镯子带在身边,放在贴身的衣袋里,有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将手潜藏在衣服里,细细抚摸那光洁的镯子。那时刻赵半窗的表情是阳光的,也是温馨的,好像他抚摸的不是镯子,而是一个如镯子一样光洁的女人。然而,内心的愉悦只有赵半窗自己知道,也只有他自己才明了他自己在守望着什么。那时刻,赵半窗也是有梦的,他的梦渐渐明晰了起来,有好几次他居然梦见自己将翡翠镯子套在了女人的手腕上。那时刻,女人的脸也不再是斑斑泪痕,而是像睡梦中的赵半窗一样一脸阳光。 赵半窗醒来的时候真就见着了那个叫红烛的女人。红烛裹着一身阳光冲进了当铺,她的脸颊红彤彤的,比那憔悴的神情不知娇艳了多少倍。紧跟在红烛身后的是那几个男人,那个屠夫大大咧咧地走在前面,捺在后面的是红烛的男人丘八。红烛又见着了那双温顺的眼睛,却又不敢正视它,她的眼睛很快涌出了泪水。红烛嘤嘤地哭了。老伙计瞥了赵半窗一眼,却不见赵半窗有什么动作。他依旧坐在那张太师椅上,左手端了茶杯,右手揭了茶杯盖子,轻轻地啜着茶,似乎铁栅栏外的一切同他毫无关系。可赵半窗心里明白,女人肯定是受了委屈的,似乎这委屈同他也扯不上关系,唯有可能的是这几个男人又来敲竹杠了。赵半窗不得不把对女人的同情藏匿在心里了。那几个男人也不做声,当铺里只剩下红烛嘤嘤的哭声。那个屠夫突然干笑几声敲碎了沉默,屠夫说,看来这女人同赵爷早就有一腿了,丘八该改名叫王八了。屠夫边说话边扭着脖子,暧昧地扫了一眼赵半窗和身后的那些男人们。那几个赌徒哄堂笑开了。赵半窗依然没有动,任由赌徒们笑着,不过他的眉头却是拧了起来。笑声压住了红烛的哭泣,红烛像是突然疯了一般,猛地朝屠夫撞了过去,屠夫猝不及防被撞翻在地。屠夫恼羞成怒,爬起来扣住了红烛的颈脖,一只手早扇在了她的脸上,有血从红烛的嘴角像蚯蚓一样扭曲着往下流。屠夫说,你个婊子,你不是说要将自己当给赵爷吗?你去说呀,看赵爷要不要你个烂货。屠夫将红烛扔在了地上,嘴巴粗粗咧咧地骂。瞧到女人滴血的脸,赵半窗再不能不理会了,看来红烛完全是寻求赵半窗庇护来的。赵半窗的心里有了莫名的怒火,脸上却是不氤不氲。赵半窗拿眼盯着屠夫说,这当人的话恐怕不该是你说的吧,怎么着也该问问女人愿不愿当,真要当了也该由着她男人来说,你是她什么人?!屠夫被话噎着了,着实恼怒,不由得又捉紧了拳头。屠夫说,还要看你赵爷有没有胆子敢当。赵半窗脸上依旧不卑不亢,话却是十分地硬朗,本当铺从来不当人,可也有破例的时候。你敢?!屠夫扬起了拳头。赵半窗却没有再接屠夫的话,只一扭身,一道亮光便擦着屠夫的耳边飞了过去,亮光钉在了门柱上,原来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小刀子,半个刀身已没入门柱里面了。屠夫只觉察耳边闪过一丝冷风,并没有发现射过去的刀子,再要动粗时却被旁边的几个赌徒拉住了。其中一个给屠夫丢了一个眼色,屠夫的眼光落在刀子上,不再言声了。 内容来自xiushui.Net 八百多块银元是老伙计用一个托盘端出来的,托盘上蒙了一层红纸,有那么一点喜庆的味道。毕竟是八百多块银元呵,老伙计端着托盘的手微微颤抖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赵爷为什么花这么多银元死当了这么一个女人,而且是赵爷坚持要死当的,凭赵爷的身份娶十个女人也不用了这许多的银元。那几个赌徒平空得了八百多块银元,又慑于赵半窗的那把刀子,一个个闷声不响地走了。只有丘八捏着那一页典当红烛的薄纸孤立在泥地上,痴痴呆呆地像个木偶。赵半窗忍不住叹了口气,心里止不住有几分酸楚。他弯腰将昏迷在地的红烛扶了起来,用一块纱巾擦去了她嘴角的血痕。红烛幽幽地醒了。赵半窗从衣袋里掏出了翡翠镯子,将它放在女人的手心。红烛愕然地看着赵半窗,赵半窗似乎没有注意到女人的神色,别了脸朝女人和丘八挥了挥手,说,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好好过你们的日子。赵半窗心中那份期盼已久的渴望不见了,他的声音里竟然有了那么一丝颓废和苍凉。红烛扑通一声跪下了,她的头重重磕在泥地上,又有血从她的前额涌出来,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红烛说,我不回去,你典当了我,我生是赵家的人死是赵家的鬼。赵爷,就让我服侍你一辈子吧。赵半窗却没有再说话,也没有回头,只朝身后挥了挥手,一个人径往里屋去了。 内容来自xiushui.Net 红烛怎么也不愿离开当铺了。不管丘八如何死拉硬拽,红烛始终跪在泥地上,一步也不愿挪动。丘八将手卡在红烛的脖子上,红烛却闭了眼,说,我死也要死在当铺里。丘八本来就没有了脸面,只有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丘八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当铺巷,似乎义宁州城的人也没再见过他。红烛最后由老伙计领着入了当铺的里院,在当铺里住了下来。 红烛就这么进入了当铺巷。巷子里的流言蜚语紧跟着沸沸扬扬了。然而,外在的热闹并没有影响到当铺里面的平静。院落里多了一个女人,老伙计并没有觉察有什么不同。赵半窗的脸是平静的,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一张太师椅,一盏水烟筒,一杯碧罗春,赵半窗就那么端坐于柜台后,吸一口烟,品一杯茶,眯半会眼,日子就从缭绕的烟雾里弥漫的茶香中散去了,散逸得有几分平平淡淡。赵半窗当初的那份渴望和惊喜敛藏得无形无影了。偶尔他也会趁着晨曦或黄昏,在当铺巷走上一个来回。在当铺巷行走的赵半窗依然是一袭长衫,一页纸扇,满脸淡淡的笑容,不紧不慢的步子,镇定而又散淡,和蔼而又有种说不出的威严。 红烛在当铺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翡翠镯子还给了赵半窗,赵半窗依然将镯子放在贴身的衣袋里,也不见多一句话。赵半窗无话,红烛也不会乱开口,赵半窗的和善让红烛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距离感。红烛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的生活里有了这份平静就够幸福的了,红烛不会也不敢有更多的奢望和幻想。红烛的心情是愉悦的,以至于她做着那些平凡而又琐碎的事情时脸上总浮着淡淡的笑容。红烛是充实而忙碌的,洗衣扫地,炒菜做饭,端茶送水,她片刻也没有停留。甚至帮赵半窗的女人擦拭身子,端屎倒尿,也陪着女人说话解闷。那做佣人的老婆子乐得清闲,常常不知避到哪个角落去了。红烛做这一切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她这么干。红烛偶尔也会走近赵半窗,替他端一盆洗脚水,拿一件换洗的衣服,沏一杯新买的碧罗春。在赵半窗跟前,红烛的步子拿捏得十分稳重,表情镇定,可止不住还是有些心慌,伸着的手免不了微微颤抖着。赵半窗却很自然,该伸手时依然伸手,一脸坐怀不乱的笃定。 xiushui.Net 红烛是脱胎换骨了,身子里的憔悴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她一脸酡颜,常伴着浅浅的笑。红烛微笑的时候,赵半窗总是微闭了双目,可微闭了双目也抵挡不住笑容的侵入。每逢这时候,赵半窗的手就潜藏在衣底下握着那翡翠镯子,像老僧握了念珠一样的捻来捻去。赵半窗免不了会想到红烛的那双手,那双手的粗糙慢慢褪去了,又恢复了本来的细嫩。想着那白若柔荑的手臂,赵半窗将镯子握得更紧了,他的渴望像镯子一样潜藏在衣服底下。然而,红烛不只是脸色红润了,她的身子骨也有了明显变化,似乎就在一夜之间红烛的腹部隆了起来。红烛怀孕了,可她的脸上没有半点喜色。红烛的眉头紧锁了起来,可再怎么锁住双眉也锁不住肚子,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藏也藏不了掖也掖不住。红烛央求老婆子偷偷弄了一剂堕胎药,想让鼓起来的肚子瘪下去。药正煎熬着,药香漫了整个院子。闻着药味,赵半窗的心就像水葫芦一样浮了起来,怎么也睡不安稳了。赵半窗不声不响地踅进了厨房,一双眼死死地盯住了正在煎药的老婆子,老婆子招架不住赵半窗的目光,嗫嚅着,红烛想把胎堕了。赵半窗什么也没说,只一脚踢飞了药罐,药汁洒了一地。 后来,赵半窗又背地里叮咛了老婆子许多事,还吩咐老婆子预备下红烛生儿育女的物什。半年后,红烛终于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有了孩子,红烛依然见不着笑容,心里好像有些灰暗。孩子满月,赵半窗吩咐老伙计订了几桌酒席,街坊邻居去了一大帮,喝酒谈笑,热热闹闹了一整天。赵半窗给孩子系了一把长命锁,锁是纯金的,黄澄澄的,很精巧。赵半窗还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少溪,红烛偷偷瞄了一眼赵半窗,见他满脸喜色,便顺了嘴叫赵少溪。赵半窗听了红烛的叫唤,也没说什么,只还了她一眼,任由着她叫去。 xiushui.Net 那个挂着金锁的孩子到底姓丘还是姓赵呢,当铺巷的流言蜚语越发喧嚣了。可不管窗外怎么喧嚣,那些话永远也进入不了赵半窗的耳朵,赵半窗似乎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散淡的时候,赵半窗会抱着孩子在巷子里转悠,听着那些真真假假的溢美之词,赵半窗的脸上竟然浮现了少见的灿烂笑容。红烛的心也随之灿烂着。有时候,赵半窗也会把孩子抱了放在美人的枕边。美人蛮喜欢孩子的,将孩子逗弄得咯咯咯地笑着。孩子咿呀学语的时候,红烛手指美人妈妈妈地教导,孩子便鹦鹉学舌地叫出一连串奶声奶气的妈妈。美人听了竟然欢喜得哭了,眼泪流了一整脸。可惜的是美人也就欢喜地哭了一回,便再也听不到孩子的叫声了。美人死了,她将一根布条子系在床头的横梁上,就那么半倚半枕地将自己吊死了。女人似乎走得很愉悦,脸上见不着一丝痛苦的表情,相反赵半窗的脸却无比灰暗,阴沉得像要拧下水来。只有老伙计没闲着,上鸡鸣寺请了一班和尚,吹吹打打,喧喧嚷嚷地热闹了七天七夜。一个美人竟然受着赵半窗如此厚待,当铺巷的老婆子们为此眼妒了好多天。 看着赵半窗晦暗的神情,红烛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美人没生孩子,红烛让少溪披麻戴孝,甚至还抱着孩子捧起了美人的灵位。丧事办妥了,喧嚷的当铺很快沉寂了下来。老婆子被辞退了,院落里的琐碎事儿都由红烛操持着。红烛越发殷勤了,一切都有条不紊。赵半窗似乎又回到了那种闲适的生活状态。一张太师椅,一盏水烟筒,一杯碧罗春,几乎又成了赵半窗白日里的全部内涵。这些都是红烛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是赵半窗潜藏在衣服底下的那只手,以及那对翡翠镯子。赵半窗有时会死死攥着那对镯子,生怕一松手镯子就会飞跑了。赵半窗的心思没有人会知道,日子依然在散淡中运转着。 内容来自xiushui.Net 红烛的心却有些不平静了。赵半窗仍然睡在美人睡过的那间房里,房间的一切陈设也没变。美人在世时是什么样子,现在依然是什么样子。赵半窗没去改变它,红烛也不敢私下动手。心里不平静的时候,红烛就会在黑暗里痴痴瞧着那扇镂花木门,想象着里面那个男人的睡姿,想象着那个男人的梦幻。甚至红烛还在门边静立过,隔着镂花的门板,男人的鼾声如水一样渗了出来。红烛用手碰了碰门板,门是闩死了的。红烛叹口气,默默回了自个的房间。红烛最终也没能走入那个房间。 生活的平静让人渐渐淡忘了许多似乎不应该淡忘的事。终有那么一天,丘八突然窜入了当铺巷,他的到来并没有丝毫先兆。在突袭当铺巷之前,丘八伙同老虎岩的土匪先袭击了九曲巷的赌坊,就在那张长条形的赌桌上他们结果了屠夫和另外几个赌徒,丘八似乎不解恨,用鬼头刀将赌徒们的手指一根根砍了下来,尔后他们背着从赌坊劫来的银元窜入了当铺巷。那会儿正是彩霞满天,落日的余辉将鱼鳞似的瓦脊染成一片金色。土匪们手提滴血的鬼头刀穿行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一阵鸡飞狗跳后,当铺巷就剩下一片死寂。丘八们就那样直冲冲地闯进了当铺,等清点帐目的老伙计发觉时土匪们早已穿过铁栅栏冲向了里院。 就像平常的傍晚一样,那一刻赵半窗正端坐于桂花树下,一桌小菜,一壶老酒,有滋有味地消受着。红烛也立于一旁,斟酒夹菜,红袖添香,赵半窗的心情暗藏了许多惬意。丘八窜进去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并不是偎着酒菜的二个人物,而是尖了屁股在院子一角玩石子的三岁孩儿赵少溪。丘八的心头冒火了,他径自捏了刀扑向孩子,孩子很快被他拎到了那桌酒菜前。丘八用刀指着红烛问,孩子叫什么。红烛的脸早已是一片苍白,慌乱间说,赵少溪,不不,是丘少溪。哈哈哈,赵少溪,果真是一个野种。丘八的声音突然变了调,怪叫了起来,他的刀也没闲着,只横里一抹,鲜红的血柱从孩子颈脖处喷涌而出。赵半窗的手摸向了腰间,那把小刀尚未出手,一个土匪的鬼头刀早落在了他的胸口上。红烛咆哮了一声,整个身子疯狂地投向了丘八。红烛尖锐地嘶叫着,丘八,你杀了你自己的儿子。红烛根本未能抵达丘八,掉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丘八闻言一怔,用刀挑开了孩子的衣衫,孩子肚皮上赫然印着一块银元大小的红色胎记。丘八的肚皮上也有着相同大小的一块红疤,丘八的父亲身上也有,那是丘八祖母偷情时给她的后代们留下的一块戳记。丘八从地上抱起了孩子的尸体,转身朝当铺口走去了,他一边走一边喃喃着,我杀了我的儿子,我杀了我的儿子。 HULING 红烛醒来的时候,当铺早已被土匪洗劫一空。她将身子一步一步挪近了赵半窗。赵半窗的脸也是一片苍白,没有丝毫血色。但他的表情是平静的,似乎没有经受任何痛苦。红烛挨近的时候赵半窗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里尚有一线暗淡的光,像微弱的火光一样摇摆着。赵半窗的嘴唇在轻轻地翕张,红烛将耳朵压在他的唇上,终于听到了赵半窗的声音。赵半窗说,画,画。他的手无力地指向了当铺的厅堂。红烛似乎明白了赵半窗的意思,她踉踉跄跄地跑向了前院。红烛很快摘来了那幅虎卧孤松的画,那画的背面却书了许多字,“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那是山谷道人的书法,笔势苍劲,肥中有骨,骨中有肉。赵半窗一字一顿地说,你把字当了,好好生活吧。红烛终于嘤嘤地哭出了声,她伏在赵半窗的耳边轻轻说着,我要为你生个儿子。赵半窗轻轻摇了摇头。红烛又说,你要好好活着呵,我一定要为你生个儿子。赵半窗惨白地笑了笑,终于合上了双眼。 ——原发《作品》杂志 简介:樊健军,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修水县作协名誉主席、顾问。小说见于《人民文学》 《收获》 《当代》 《钟山》 《上海文学》 《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等刊,著有长篇小说《诛金记》 《桃花痒》,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 《向水生长》 《穿白衬衫的抹香鲸》 《空房子》《行善记》 《有花出售》 《水门世相》等,曾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第二十九届梁斌小说奖,《飞天》第二届十年文学奖,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星火》优秀小说奖,《青岛文学》第一届海鸥文学奖,江西省文艺创作奖,江西省谷雨文学奖,江西省作协“天勤杯”2021年度优秀小说奖,作品入选加拿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名单。 |